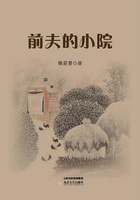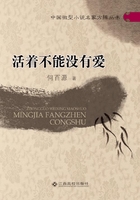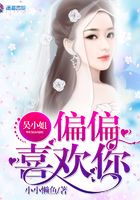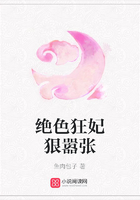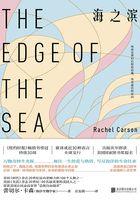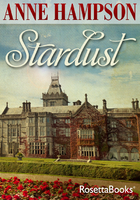所谓兔死狐悲,杜重威被处死的消息传到河中后,时为河中节度使的李守贞当时就坐不住了。他心想,他乃中渡叛国的帮凶,汉人对他也恨之入骨,汉朝廷又怎会放过他呢?因而,他每日里忧惧不已。赵思绾叛乱的消息传到他耳中后,他的心思就动开了:这些年来,靠着从杨光远手里夺得的巨额财富,他对士卒经常大加奖赐,深得士卒之心,在军中威望一直很高;汉朝廷刚刚建成,新天子又年少初立,朝中的执政大臣不过是一些后进之辈,他一旦起事,朝廷根本就拿他没有办法。于是,他一面加紧招纳亡命之徒,蓄养敢死之士,修建城防堑壕,缮治战甲兵器;一面遣密使前往辽国,以蜡丸书与契丹相交。
不想,李守贞的密使被边吏捕获,并被押到大梁。然而,朝廷虽然拿到他与辽人结交的证据,但因对他有所顾忌,不但没有对他问罪,反而一直姑息安抚。如此一来,李守贞对朝廷就更加轻视,反倒变本加厉、更加猖狂了。
浚仪人赵修己善于术数,李守贞镇守滑州之时,慕名将其聘为司户参军,自那之后,赵修己就一直跟随他。李守贞知道赵修己善于听音识吉凶祸福,便请他到家中为家人听音。
赵修己到李府后,李守贞让自己的夫人、儿子、女儿、儿媳皆到赵修己跟前说话,但赵修己一直没有吭声,而且脸露忧色。不想,李守贞之子李崇训的夫人刚一开口,赵修己就忍不住惊呼道:“此乃天下之母也!”
李守贞一听,心想:“我儿媳犹为天下之母,我取天下又有何疑?”
李守贞的这位儿媳,也就是李崇训之妻符氏,乃符彦卿之女,闺字玉娘。
不过,赵修己对李守贞说道:“令公儿媳固然贵不可言,令公却毫无人主之音。”劝他不要造反,并说道,“时命不可,千万不要轻举妄动!”此后,又多次切谏,但李守贞主意已定,根本听不进去。赵修己无奈,只好诈称有病,辞职回老家去了。
僧人总伦以术数献媚于李守贞,言称他命中注定为天子,李守贞信以为真。为了收服众心,他特意召集众将佐饮酒,并在酒宴之上手持弓箭,指着《舐掌虎图》说道:“我若有非常之福,当一箭射中虎舌。”果然,一箭射出,正中虎舌,左右皆向其称贺,李守贞也因此更加自负了。
恰在此时,赵思绾遣人为李守贞送来一件黄袍,说是在长安旧宫偶然所得,请其起兵举事。李守贞大喜,自认为天人相合,大事必成,遂自称秦王,以判官靖余、孙愿为丞相,以从事刘芮为枢密使,以总伦为国师,并加封赵思绾为晋昌节度使。
同州节度使张彦威一直对李守贞心存疑忌,因而,李守贞的一举一动,他都及时地奏告朝廷,并请朝廷早做防备。朝廷见李守贞反状已露,遂命滑州马军都指挥使罗金山率其所部戍守同州。
陕州节度使赵晖一接到改任他为凤翔节度使的诏命,即率军离开陕州,前往凤翔赴任。李守贞闻讯,当即遣其骁将王继勋率兵占领潼关,以阻止赵晖西进。赵晖闻报大怒,当即率军猛攻潼关。潼关守关将士此时尚不愿与朝廷为敌,大都不肯卖力,因而,赵晖轻而易举地就把潼关攻占了。
王景崇接到朝命后,不但找各种借口不离开凤翔前往邠州赴任,而且以征讨赵思绾的名义征召邠州兵前往凤翔。暗地里,他又致书蜀凤州刺史徐彦,请求互通贸易。蜀主孟昶当时就明白了他的用意,连忙命徐彦回书招降。王景崇接到书信,当即遣使请求归附蜀国,孟昶遂将凤翔改为岐阳军,以王景崇为岐阳节度使、同平章事。与此同时,王景崇又密与李守贞来往,并接受了李守贞任命的官爵。如此一来,他已“脚踏三只船”,心中顿觉踏实不少。
其实,不仅王景崇如此,就连朝中的不少大臣也与李守贞暗地里结交,以留后路。
汉朝廷闻听李守贞已公然竖起反旗,这才奏请新天子刘承祐颁下诏书,削夺李守贞的所有官爵。
长安赵思绾、河中李守贞、凤翔王景崇的相继叛反,让朝廷上下、京城内外顿时乱成一锅粥。一时间,朝野之间、道路之上,各种传言甚嚣尘上。
农主
小皇帝刘承祐忧心忡忡,遂召四位托孤大臣商议对策。郭威安慰道:“陛下勿忧,三镇既想叛反,早晚都是免不了的。晚反不如早反,逆臣们趁着先帝大丧发难,必然不得人心,只要处置得当,平定三镇只是早晚的问题。”
史弘肇沉声说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逆臣造反,出兵平叛就是了,何必忧烦?陛下给臣一张军令,不出三月,臣就会把三个逆臣的首级给陛下带来!”
史弘肇为人孤傲寡言,而且掌典着朝廷军权,新天子又对他格外信重,苏逢吉、杨邠本就对他心存疑忌,再加上史弘肇一直对文臣们颇为轻视,若再让他统兵平叛,一旦功成,他的威权就更大了,到那时,满朝之中恐怕就再没有人能制约他了。因而,史弘肇话音刚落,苏、杨二人就不约而同地说道:“史公乃先帝托孤重臣,怎可轻离朝廷?”
郭威也道:“二公所言极是,不如先遣三路军马分赴三镇,摸摸三镇的虚实再说!”
刘承祐也不想让史弘肇离开朝廷,遂依照郭威建议,派发了三路大军:第一路,以澶州节度使郭从义为永兴行营都部署,以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尚洪迁充行营都虞候,率侍卫军兵发长安,讨伐赵思绾;第二路,以陕州节度使白文珂为河中行营都部署,以奉国左厢都虞候刘词充都虞候,以客省使王峻为兵马都监,出兵河中,讨伐李守贞;第三路,命赵晖、药元福、李彦从会军,共同讨伐王景崇。同时,又任命工部侍郎李谷充行营都转运使,负责三路军马的粮草转运。
朝命刚刚发出,北部边境突然传来好消息:孙方简遣使者到大梁,请求归降朝廷。
原来,辽人北归之时,耶律阮曾任命孙方简为定州节度使,后来,辽国境内屡屡发生叛乱,耶律阮一直忙着四处平叛,根本就无暇与中原相抗了。孙方简认为,定州紧邻着镇、魏,汉朝廷一旦稳定,必会出兵攻伐他,于是便率其部属三千多人退回狼山故寨,分兵控守要害。此时耶律郎五和麻答皆驻军于定州,闻听孙方简不辞而别,大为恼怒,屡屡出兵攻袭狼山故寨。孙方简见情势危急,只好遣使归降中原,请求朝廷出兵救援。
汉朝廷当即下诏恢复了孙方简的所有官职,并以刘在明为幽州道马步都部署,出兵北上,帮助孙方简经略定州。
消息传至定州,耶律郎五、麻答大惧,当即将定州焚掠一空,驱赶着城中之人北回辽国了。等孙方简听到消息率众赶到定州之时,定州已空无一人,满眼都是瓦砾与灰烬。
孙方简随即奏请以其弟孙行友为易州刺史,孙方遇为泰州刺史,以成鼎足之势,朝廷答应了他的奏请。自此之后,辽人每次入侵,孙氏兄弟都会相互接应,因此,辽人对孙氏兄弟是又恨又惧,但无可奈何。
至此,晋末被辽人攻占的州县,已全归汉朝廷所有。
麻答回国后,辽帝耶律阮对他失守中原大为不满,想要对其治罪。麻答不服,说道:“这能怪我吗?要不是先皇帝任用汉人为官,能有今天的恶果吗?”耶律阮一时难以辩驳,但最终还是把他鸩杀了。
此时,晋少帝石重贵与李太后正居住在辽阳以北二百里处,耶律阮命他们迁往辽阳暂住,石重贵甚为感激,连忙遣人向耶律阮致谢。耶律阮大为高兴,并命人按时提供一应用品。不久,耶律阮也抵达辽阳,石重贵与李太后、冯皇后连忙前往谒见。石重贵欲身穿素衣,头戴纱帽,耶律阮则准许他身穿常服相见。石重贵见到耶律阮后,趴在地上,连连向耶律阮认罪。耶律阮命左右将石重贵扶起,温言抚慰,并设宴款待。
跟随在耶律阮帐下的晋朝大臣及教坊内人,一看见中原故主,皆不胜悲痛,呜咽不止,纷纷献上衣帛药物。不久,耶律阮离开辽阳,临走之时,向石重贵要走了十五名太监、十五名大臣,皇子石延煦也被他带走了。
耶律德光的妻兄禅奴,因长相丑陋,智力低弱,迟迟没有娶亲。耶律阮听说石重贵有一幼女,便为禅奴向石重贵求婚。石重贵不愿,只好以女儿年幼为由,婉言推辞。耶律阮竟然遣骑军硬是将石重贵的幼女夺过去,赐给了禅奴。
李太后、石重贵心痛欲绝,但又无可奈何。此后,又有辽人不断骚扰,耶律德光之子述律王夺走了石重贵的宠妃赵氏、聂氏。
李太后又亲自去见耶律阮,请求在汉人城寨旁边赐给他们一块土地,耶律阮答应了她,准许石重贵与李太后迁往建州居住。建州节度使赵延晖听说此事后,对石重贵一行以礼奉迎,并请石重贵居住于衙署之中。不久,他即奉辽帝之旨,在离建州城数十里的地方,划给石重贵五千多顷的土地。
至此,石重贵一行终于安定下来,建筑房舍,分地耕种。两年后,李太后病逝;十八年后,晋少帝石重贵也逝世了。
后人有诗叹道:
大眼不忍看国残,抗辽哪问时维艰。
辽主阳城奚车失,虏骑澶州腥血溅。
十万铁剑变虚话,三千江山成空叹。
还乡桥上极目望,农主何必泪涟涟。
长安、凤翔、河中三叛并举,声势日盛一日,而就在这非常之时,朝廷又发生了内讧:宰相与枢密使的权力之争愈演愈烈。
苏逢吉、苏禹珪、窦贞固、李涛四位宰相,各举亲信,致使朝廷人满为患。杨邠担心官吏太多会虚耗国用,故而,经常将宰相所举奏的人选驳回,众宰相自然大为不满。李涛甚至想把杨邠、郭威两位枢密使外放出京,上疏奏道:“如今关西纷扰不宁,外御当为急务。二枢密使皆为先皇钦定的佐命功臣,官位虽然尊贵,但家里并不富裕,倒不如授给他们要害大镇。至于枢机之务,完全可以让逢吉、禹珪办理,他们跟随先帝多年,皆可委任。”
小皇帝刘承祐不明就里,想都没想就答应了。杨邠、郭威听说后,连忙求见李太后,泣诉道:“臣等跟从先帝起于艰难之中,如今,天子却听人之言,欲将我等抛弃于朝廷之外。何况,关西正有大事,臣等又怎么忍心自取安逸而不顾社稷呢?若臣等确实不能胜任,也须等先帝大葬完了再说啊!又何必这么着急就把臣等抛弃呢?”
李太后当即把刘承祐叫到跟前,大声呵斥道:“杨邠、郭威皆为国家勋旧之臣,先帝尚未安葬,你为何就急着要逐走他们?”
刘承祐嗫嚅道:“这……这都是宰相们的意思,我哪想赶他们走了?”
李太后随后又把四位宰相召到跟前,质问道:“为何要赶走二枢密使?是谁的主意?”
李涛倒是敢作敢当,朗声说道:“这个上疏,是微臣一人所为,与他人无关。”太后大怒,当着他的面就让刘承祐罢免了他的宰相之位,让他回家反省。
刘承祐见太后为此事竟然生了这么大的气,便与左右商议,想更加重用两位枢密使,以向太后表明这确实不是他的意思。左右之人早就对二苏专权不满了,皆想趁机削夺二苏之权,重用杨邠、郭威。刘承祐遂让杨邠、郭威既为宰相又兼枢密使,李涛之位,则让三司使王章顶替。
自此,政事皆委托杨邠,军事则委托郭威、史弘肇,财政则委托王章,而原先的三位宰相——苏逢吉、苏禹珪、窦贞固,则权力尽失,成了百无一是的摆设。
如此一来,杨邠反倒成了朝廷政事的真正决策者,无论大事小事,只要杨邠不同意,谁都不敢施行;任用官吏,若是杨邠不点头,哪怕是主簿、校尉之类的小官职,也休想任命。但是,杨邠权重事繁,经常无暇顾及,致使许多政事都被搁置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