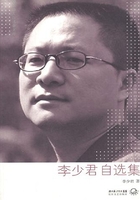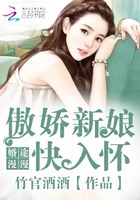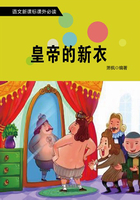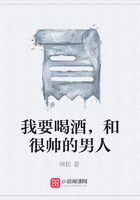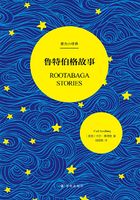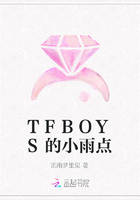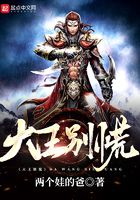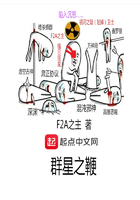我们畏惧死亡,是因为在我们既定的价值观念中,死亡是不可以用其他方法超越的。一旦死亡来临,便是无法挽救的。而如果一个人,他将道义、爱情、责任看得比死亡更重要,当现实的情形不容许他享受和承担的时候,死亡即结局。说起来很有意思,一个人选择死亡是因为他没有那么看重死亡,而选择的结果却是他必须接受死亡的到来。经历过这个结果的,就再也没有办法和活着的人分享这份经历;而没有经历的,起死回生的,却不能算作真正地经历过死亡。这看起来是一个悖论,却也是一个关于生命和伦理道义的永恒命题。它使得死亡更加神秘。
一个如此珍视艺术和美的人,是多么不忍心被一群“另类”的群体所折磨!而这折磨的唯一终结的方式就是死亡。他们将尊严和对美的追求看得比生命还重,所以就选择了死亡。这个时候难道不值得我们仰望么?
一直羡慕那些从“文革”活过来的人,尤其是那些原本拥有很多敬仰却一下子全部失去的文人和艺术家。我甚至怀疑是什么力量让原本心态优越的他们渡过难熬的时期,从一片黑暗中望见未来。
对此杨绛先生给了一些答案。有人评价说,这位老人把尊严看得很重,主要因为她信仰文化,她不相信,几年前宝贵的文化会被暴力毁灭。杨绛先生,怀着对文化的坚定的信仰,渡过了人生的寒冬,迎来了暖阳。这又是另一种境界了。
现代社会已经开放到不惧谈生谈死,也不回避性和暴力。但是你会发现,在人的内心深处,总是有一些东西是无法逾越的。那种微妙的感觉,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会懂得。人活着,可以有很多理由。而死亡,只需要一个理由就够了。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解释,为什么有很多人苟活于世,并从未发觉;而那些选择绚烂至极去死的人,却创造了历史。
可是为什么偏偏要选择死呢?活着,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啊。可是,无论做多少假设,我都无法理解诗人殉道式的死亡,无法理解那些被人为设置的障碍扼喉而亡的志士。也许,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不被大众接受。他们才在有生之年和逝去之后无比孤独。可就个人而言,我尊重他们的选择,不会像曾经那样嘲讽或是不屑,单纯从一个角度去解读生死。
生是无法自我掌握的,死却可以。
这并不能证明生比死更加伟大和神圣。只能说,我们的命运之初是单纯的形式,不受个人左右的,可是其间漂泊的整个过程,就是我们可以略微掌握的了。我讲“略微”,是因为还有很多人力不敌境遇的尴尬处境,是由世间的其他元气所左右的。因此敬畏死亡同敬畏生命一样让人感动。
台湾作家刘墉在他的作品《萤窗小语》中说:“幸而在这当中,我们还能有些作为,使自己平凡地生,却能伟大地死;在母亲一人的阵痛中坠地,却能在千万人的哀恸中辞世。”不知道为什么,对于这句话的印象尤其深刻。我曾在初中的语文课堂上说出这句话。结果被老师打断。因为确实,在生得最绚烂的年纪里谈死是一个禁忌。而我不小心打破了这个禁忌。
曾经有一段时期,我总是乐于思考人之于宇宙的关系,开始好奇茫茫宇宙间人的生存是多么偶然和不易。甚至经常在物理课上走神发呆,问一些没头没脑的问题。15岁左右的年龄,仿佛轻而易举地就可以将死亡挂在嘴边,自以为是一件很勇敢很伟大的事情。
六岁的时候,奶奶在老家过世。当时还不懂“过世”的含义。只知道过年的时候,家庭的团聚里少了一个慈祥和蔼的老人的身影,于是猜测奶奶一定是走很远的路去很远的地方了。可是没有人告诉我:什么是死、死的背后是什么。
我们往往喜欢将死亡粉饰成壮烈的样子,并借以支撑某种理想。因此就造成了很多对死亡本身的误解。比如,小学的时候,课文中写董存瑞舍身炸碉堡、黄继光堵枪眼、邱少云被敌人的燃烧弹活活烧死也纹丝不动的英雄事迹时,我以为死亡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那时候甚至坚信,假如有一天自己也被放置在这样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也会用同样的意志完成使命。长大之后才慢慢知道,其实一些死亡是惨烈的,并不如课本里写得优美。而我自己必须承认,永远达不到火烧在身上也纹丝不动的境界。
另一种不惧怕死亡的是参透了死亡的人。他们淡去了红尘是非的争执,身无所羁。其实这一类人心中是承受过巨大的痛苦的,不然难有这样的造化境界。他们是从一个痛苦的极端回头,去寻找平凡和平淡。活着和死,对于他们而言从本质上说,并没有太大差别。虽然歆羡那些参禅悟道的高人,却也深知自己六根难静,到底是剪不断对这个世界丝丝缕缕的牵连。
当你没有思考死亡的时候,生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情。而有一天,你开始思考死亡了,就不禁会怀疑,生的价值在哪里,生和死的抗衡点是如何在短促的生命进程中得以实现的。生命就如同一场接力比赛,一代一代的人们完成着这样的接力赛,也不断续写着不同的故事。欣赏这些故事本身,就是一种愉悦。那么死亡就没那么可怕了。
2007年2月
(原名《老与死亡的边界》,选自《记忆是一种抵抗的姿态》,北方文艺出版社,2011年9月。有删改。)
枯叶蝴蝶
这个答案会帮助我们在枯燥的日子里坚持年轻时的梦想,在遭人误解或者是陷入尴尬境地的时候保守一点理想,即便是你的世界崩塌了一切可以依赖的东西的时候,也可以有一种叫信仰的圣物支撑着你的精神,让你心中还留有哪怕一点的光亮。
美的憔悴而伤感,将小小的宇宙隐匿在翅膀下,却在迷醉自我之时命丧黄泉——小小的枯叶蝴蝶,你的衰颓到底是人类的缩影,舞蹈着隔了一个寒冬的苍凉,给自己的灵魂,还有你生命的杀手——人类。
颓败在自然界当中堪称是一种艺术。盘曲的虬枝、凋零的花叶、残衰的荷叶是自然赋予生命的另一种迥异的诠释。然而,蝶的颓败呈现出的并非仅仅是它隐藏了粉饰的华丽和光鲜的色泽,也不仅仅是它翩翩飞翔时蕴藏的静默,更是一种极大的伪装。
任何生物都有伪装的本能。野兔毛色的变化,变色龙对身体颜色的神奇调配,还有竹枝虫细挑、硬挺的灰褐色躯体,无一不是伪装。伪装使得它们轻松地逃脱敌人的追捕而获得重生的权利;也使得它们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波澜不惊的惬意生活。却也恰恰是伪装,褪去了它们天生具备的警觉感官,而将小小的内心世界虚掩起来,企图呈现给他人另一副模样。
不可否认,自然、天性、淳朴,在伪装中渐渐淡化,而最终成为梦幻世界中难觅的渴求。自然的神奇之处在于它造就了种种合乎自然逻辑的神秘,而却将神秘掩盖起来期待着观者的察觉。在广袤的非洲草原或是南美的热带雨林中,每一个物种都为着自身的生存绞尽脑汁地谋划着。不同的是,有的是上天自然的赐予,有的则需要生物本身兼具机警与幸运,才能有幸逃脱敌人的捕食。而我们欣赏自然,并为之沉醉,也许就是因为自然的某种法则暗含了人类社会竞争的片段,在解读自然界的弱肉强食的时候,我们也仿佛享受了一回“暴力美学”,发现了人类社会的一点影子。每到这个时候,你才会惊异于人类的命运与自然如此紧密的契合,你才不会自大到误认为人类早已经伟大到可以创造自然的地步。这就是我们研究和发现自然奥秘的动力源头之一。
记得小时候经常喜欢去动物园参观。那个时候认为动物园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缩影和佐证,也喜欢憨态可掬的动物被圈养在人可以触及的地方,以增加童年时接触的快感,满足萌动的好奇心。长大以后,越来越害怕去动物园看那些动物。不知道为什么,每次看到一个原本属于自然的生物被圈养,接受着人类的喂养和照顾,当然还连带着毫无顾忌的观看和议论。总觉得它们原本丰满的生命里少了些什么。走过圈养着猛兽的“领地”,人类不免带着些不可一世的态度冷冰冰地傲视那些被驯服的动物。大家争相讨论它们在笼中看似焦虑的踱步有何寓意,它们冷漠的眼神背后藏着些什么。甚至学着虎的叫声对着一只活虎叫嚣。虎原地不动,甚至头也懒得转一转。它背对着傲慢的人类,面向山间一抹残阳,冷峻而孤寂。那情形让人不免唏嘘:究竟是人类宣称自己的权力,还是在炫耀自己的愚蠢?有时候,未尝担忧人类最终的命运会不会被另一个更加强大的物种“圈养”,而如同今日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寄人篱下,天性消弭。
就如同这可怜的枯叶蝴蝶一样,它在伪装中失去了生命,被陈列在博物馆的角落里供人观赏,甚至被把玩着已经失掉灵魂的身体。人们把它捏在手里的时候,已经不觉得有任何不忍。他们以为,那不过是一片枯叶,不足为惜。
娇小易逝的生命,还有那片为了掩盖生成的“枯叶”呵,你能否以你脆弱的身躯求得人类的一点怜悯,告知他们你生命消殒的讯息?人类把玩的,不仅仅是瘦小的躯干,更是你们曾经的和未来已经逝去的梦幻?
蝶的翅膀犹如人的外表,只不过它暗合了某种比人类社会简单的法则以求得最基本的生存权利。蝶的翅膀用枯败的逼真模样维护着自己,人用谄媚的奉承保护自己。蝶的翅膀下喁喁私语的心,念的仍是自然灵性的渴盼与皈依自然的祈祷;人的心中默念的也不过是万物归真,天人合一的终极夙愿。
可惜我们太容易被华丽的表象所吸引,太容易沉醉在一个无法人为变更的标准中去衡量这个世界。人是视觉的动物。有时候不可避免地因为外表的丑陋或平常就忽视了内在的涵养。就如同因为一句漂亮的文章,就忽视了它所要表达的含义一样。记得我读高中的时候,一位年近六旬的语文老师曾经语重心长地告诉我说,语言是很神奇的,再华丽再炫的语言到最后都会回归到最简朴的方式,因为在一些时候,表达的形式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重要。
就如同武术中的花拳绣腿并不能抵抗切中要害的攻击一样,绘画中万变的笔法也不比不了寥寥几笔的勾勒来得明了自然一样。刘墉先生说:“万变的道理不过是个‘零’字,大动的终结不过是个‘静’字,最广的境界不过是个‘心’字。”追求简单的生命、简朴的生活,本身就是极其动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