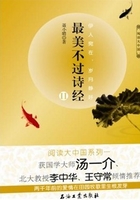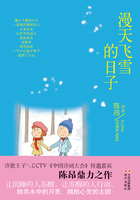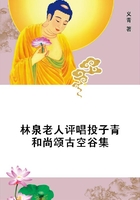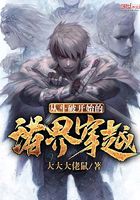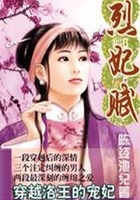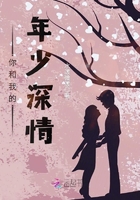首先,孤独是同生活的个体感受紧密相连的,最深刻的当属在陌生城市(空间)的漂泊与境遇。莎乐美这样回忆里尔克在巴黎承受的孤独:“里尔克第一次逗留巴黎期间,那种痛彻心扉的矛盾以及就是的恐惧强烈地爆发出来,这种矛盾使他从群体走向孤独,又在孤独中走向内心的分裂。”[166]最可怕的孤独不是一个人的孤独,而是人群之中的孤独。里尔克一面享受着孤独带给他的万千思绪和喷薄而出的灵感,一面承受着被孤独吞噬的内心。他为了克服过分的孤独给他带来的至死幻灭感,于是一次次走向人群,无论是走向实在的人群还是通过书信和联络让自己置身于人群中。可惜一次次的尝试均在孤独漫涌上心头的那一刻成为泡影。成为他一个人不可避免的悲剧。对于里尔克在城市间的漂泊者角色,霍尔特胡森曾经这样形容:“在马不停蹄地寻找心中真正的故乡、上下求索试图确定人在宇宙间的方位和归属的同时,他又将孤独感奉若神明,对他来说,孤独感甚至是创作的必要条件和保证。”[167]可以说,时时处于这种矛盾之中的里尔克希望找到灵魂上的依靠,以便安放他“擅于”孤单的心。于是他写:“那里雄伟的修道院宛如华服/围裹着不曾生活过的生命。那里我愿意置身朝圣者之中,不再有欺诈能够将我/同他们的音容阻隔,那里我愿追随一个失明的老者/走无人识得的路。”(《让我成为你的辽远的守望者》)[168]诗人愿意选择的,远远超出一个人的精神范畴,而是囊括了对一个时代人心迷失的全部担忧。诗人甚至直抒胸臆地在《孤寂》一诗中说:“当一无所获的身躯分离开来,失望悲哀,各奔东西,/当彼此仇恨的人们/不得不睡在一起:这时孤寂如同江河,铺盖大地……”[169]人们渴望肉体的欢愉、渴望通过精神的相互依偎得到安慰,可惜事不随人愿,尝试往往以失败告终。最终的最终,人类还是需要依靠自身的思想克服孤独,走向死亡。这是作为诗人和哲人的里尔克早已预见的,也是他因为敏感必须加倍承担的东西。他一面承担着孤独,一面为人们的不了解而感到惋惜:“世界上的人根本不了解孤独的实质意义,只是一味地憎恨孤独的人。”[170]他甚至从乞丐的视角不无新意地写道:“我叫喊只为了极少极少,诗人们却为了更多才呼号。”[171]诗人就是这极少数承担者之一,却是为了更多才呼号。为的是众生灵的觉醒,为的是人类对于自身处境的更加清醒的认识,为的是将自己绝然于世间的灵魂安顿,然后照亮黑暗的尘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里尔克的身份不仅仅是一位诗人、或者是一位哲学家,而成了一个救赎者。他也自知承担着诗人和艺术家的光辉使命,因而为了艺术的纯洁愈发孤绝下去。正如他所言:“只有当个人穿过所有教育习俗并超越一切肤浅的感受,深入到他的最底部的音色当中时,他才能与艺术建立一种亲密的内在关系:成为艺术家。”[172]的确,在完成《马尔特手记》之后,里尔克对孤独有了更深层次的体悟。在给莎乐美的信中,他说:“在漫长复杂的孤独中,常常可以达到极致,《马尔特手记》便写于那时,我很确信我付出中的能量来源于,在卡普里那些无数个相安无事的夜里……”从1902年到1909年,诗人和巴黎这座看似繁华实则孤单的城市相拥,结果只是愈发地孤独。他无数次地在书信、诗句和日记中提及那种莫可名状的孤独感:“巴黎……是一座十分沉重的、令人恐惧不安的城市……街道的冷酷和杂乱,院子、人与物的不自然,使人们不得不忍受这种折磨。巴黎……给人以某种无以名状的恐怖。它完全迷失了自己,就像一颗脱轨的行星,朝着某个可怕的相撞飞去。”“现在我处在人的群体之中,再次感到了孤独,我所遇到的一切都显得多么虚假。”(1903年7月18日致莎乐美的信)[173]
其实,巴黎和俄罗斯是诗人里尔克的第二故乡。除了巴黎给他带来的无法克服的恐惧和幻灭感之外,俄罗斯则成了他在遇见巴黎之前的精神归属地。在至艾伦·凯的信中,里尔克说:“那里(指俄国)的人们很少注意时间和有时间性的东西,因为在那里总有未来,每一时刻的消逝都更接近永恒。”(1903年4月3日)[174]里尔克向往的,是脱离了现代化进程中被人为压缩了的空间,被规划和被约束的时间。这样就引到里尔克的第二层孤独上来。
其次,孤独是同时间的绵延带来的虚无感紧密相关的。曹元勇在《马尔特手记》的“译后絮语”中说:“对于里尔克。他对这种生活方式的选择,与其说是决绝的、义无反顾的精神意志的强求,不如说是一种宿命,一种冥冥之中对纯粹是人之存在的渴求。”[175]这种如同皈依宗教一般信奉的孤独成为里尔克诗歌中除了死亡之外的又一大主题。《这村里》一诗扑面而来的孤独感让人心悸:“这村里站着最后一座房子/荒凉得像世界的最后一家。这条路,这小村庄容纳不下/慢慢地投入那无尽的夜里。”[176]诗人近乎绝望地写到这座世界上最后的房子,即立于时间尽头的一种荒谬的存在。无论人们是否承认这种存在,在诗歌的领地里,绝对是诗歌的权力,也是里尔克借以表达绝望的最佳工具。除此之外,在《抛开双翼回故乡》一诗中,诗人写:“……时间恰如书页上/一角枯萎的边缘。时间是已然被上帝抛弃的/一领闪光的衣衫……”[177]时间和空间是这个世界得以存在的最基本寄托,也是人们赖以寄托心灵的最好去处。可是在里尔克那里,连时间都已经枯萎,似乎受到上帝的抛弃。在不可捉摸的神性之上,人类一切自我存在的本体都仿佛已经消亡,只留下空荡荡的思考,以及绵延于人群之中的孤独的爱,才使得万物得以延续。在给德国女画家褒拉·门德尔松·贝克尔写的《安魂曲》中,里尔克如此慨叹:“……因为你/已经习惯另外的尺度,你觉得/这只是一瞬间的事情;但是/如今你置身于时间,时间是漫长的。时间流走,时间增长,时间/恰如一场沉疴的一次复发……”[178]这让人不由得想其波德莱尔笔下的时间。在波德莱尔的散文诗《双重屋子》中,描摹了诗人吸食毒品时产生的幻象以及在清醒过后的绝望感。他近乎神经质地写道:“啊!是啊!时间又出现了;现在时间又称王了……回忆,悔恨,痉挛,害怕,焦虑,噩梦,愤怒和神经官能症。”[179]可以想象,在诗人吸食大麻之后,时间成为一种空缺,而诗人在这样的精神悠游中无比陶醉。但是在意识恢复之后,又是让他恐怖和躲藏不过的时间。在这一点上,里尔克同波德莱尔是相似的。他们都是在空无和精致的时间中迷失的孩子,他们紧张、恐惧、歇斯底里,无意要留住时间,却深受其遗留的孤独的折磨。用莎乐美的话说:“他对外界没有安全感。确切来讲,他说到底就像只器皿,那些不可避免的将要从外部黏附自己、把自身包围的饰物,绝不可能以任何一种方式进入内在的体验。”[180]
最后一个层次的孤独是更加厚重的历史感,带有超脱于个人情感和体验之上的人类共有的宿命意味。也正是这个层次上的孤独让里尔克呼吁“请您爱您的孤独,把孤独以悦耳的悲叹给你造成的痛苦承担起来吧”。[181]在这个层面上,诗人将个体的孤独化解在宇宙的孤独之间,因其不可逃脱和永恒存在而变为一种必将承受之物,因此享受和爱是不可缺少的。正是以此为契机,里尔克找到了更广意义上的自我延续,意义的延续,包括生与死。在《给青年诗人的十封信》中,里尔克写:“亲爱的先生,所以你要爱你的寂寞,负担那它以悠扬的怨诉给你引来的痛苦。你说,你身边的都同你疏远了,其实这就是你周围扩大的开始。如果你的亲近都离远了,那你的旷远已经在星空下开展得很广大;你要为你的成长欢喜……”[182]诗人借由孤独找到了与宇宙间旷远性的关联,也找到了安顿自我、延续自身有限肉体和灵魂的通衢!多么令人欣喜!当然,诗人也不乏理智地解释他之于艺术家地位和角色的理解:“艺术家一旦找出他活动生长的中心后,最重要的事就是停留在那中心里,并且绝不向外踏出半步(因为那里是他本性的中心,也是他世界的中心),停留在安静且不断对外萌芽的自我创作内层中。”[183]在此之前,诗人不无遗憾地说:“世界上的人根本不了解孤独的实质意义,只是一味地憎恨孤独的人。”[184]
因为以上这三层意义上的孤独,诗人转向最脆弱也最坚强的自我省思,又因为无法遏止的恐惧和孤独,里尔克选择了一种稀有的、决绝的、为人所不解的路。在这条路上,他渴求的是在短暂而脆弱的万物之间开辟一方空间得以安放失落的灵魂;他追求的是在他的诗句中将那些生动的、被体验过的、却正在消失的了解我们的事物做最大程度的还原;他的理想是我们这个脆弱而善变的自身找寻到一部分本质参与到无形之物中,从而在宇宙间找到出路。
这出路——是人类共有的出路,也是里尔克用尽心血不断开辟和挖掘的东西。
这出路——建立在不断抛却的抒情诗传统之上,浸润着世代诗人哀怨和愤慨的热泪。
这出路——让里尔克这个在世时备受孤立的孤绝灵魂,在死后受人景仰,并永恒地将生命延续。
这出路——就是再一次将我们都变成尘世的转换者,我们的整个此在,我们爱情的腾飞与降落,一切都使我们有能力完成自我的反思,完成终极意义的灵魂救赎。
愿玫瑰与热血与诗人同在。
注释
[1].洪帆,张巍,主编.法国新浪潮.现代出版社,2004,5:329.
[2].李晓君.巴黎的焦虑:五点到七点的克莱奥.当代电影,2004(3).
[3].吴珮慈.永恒的影像拾穗者——艾格尼斯·娃达.2001年第8届台湾女性影展资料.
[4].艾利森·史密斯.阿涅斯·瓦尔达.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1998:61.
[5].叶廷芳主编.卡夫卡全集(10卷本),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238.
[6].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354.
[7].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355.
[8].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355.
[9].叶廷芳,主编.卡夫卡全集(10卷本).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239.
[10].阿尔伯特·莫德尔.文学中的色情动机.刘文荣,译.文汇出版社,2006:6.
[11].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357.
[12].叶廷芳,主编.卡夫卡全集(10卷本).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241.
[13].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356.
[14].叶廷芳,主编.卡夫卡全集(10卷本).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242.
[15].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361.
[16].叶廷芳,主编.卡夫卡全集(10卷本).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248.
[17].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361.
[18].郭宏安,译.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300.
[19].波德莱尔,著.钱春绮,译.恶之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175.
[20].汪峰.解读波德莱尔.当代小说,2004(9):56.
[21].李斌.以北岛为例谈当代文学中理想主义的流浪意识.邢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26(6):92.
[22].刘小枫.这一代人的怕和爱.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242.
[23].钱超英.流散文学与身份研究——兼论海外华人华文文学阐释空间的拓展.中国比较文学,2006(2).
[24].爱德华·萨义德.流放随想.外国文艺·译文,2005(6).
[25].北岛.失败之书.北岛散文·自序.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
[26].波德莱尔,著.钱春绮,译.恶之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217.
[27].波德莱尔,著.钱春绮,译.恶之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223页
[28].本雅明,著.张旭东,魏文生,译.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北京:三联书店:158.
[29].普鲁斯特.论波德莱尔.新法兰西评论(16),1921,6:652.引自《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
[30].本雅明,著.张旭东,魏文生,译.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北京:三联书店:68.
[31].波德莱尔,著.钱春绮,译.恶之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203.
[32].波德莱尔,著.钱春绮,译.恶之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34.
[33].波德莱尔,著.钱春绮,译.恶之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