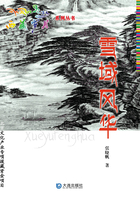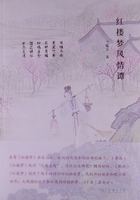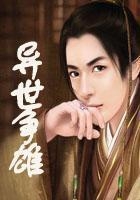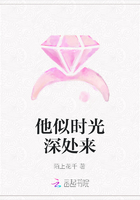无穷的追求[本文为《林语堂自传》一文中的第九节,原作为英文,由工爻翻译。]
……
林语堂
有时我以为自己是一个到异地探险的孩子,而我探险的路程,断是无穷期的。我四十生辰之日,曾作了一首自寿诗,长约四百字,结尾语有云:“一点童心犹未灭,半丝白鬓尚且无。”(《论语》四九期)我仍是一个孩子,睁圆眼睛,注视这极奇异的世界。我的教育只完成了一半,因关于本国和外国仍有好多东西是要苦心求学的,而样样东西都是奇妙得很。我只得有一知半解的(直译:半煮熟的)中国教育和一知半解的西洋教育。例如:中国很寻常的花卉树木之名目我好些不晓得的,我看见它们还是初次相见,即如一个孩子。又如金鱼的习惯,植兰之技术,鹌鹑与鹏鸪之分别,及吃生虾之感觉,我都不会或不知。因此之故,中国对于我有特殊的摄力即如一个未经开发的大陆,而我随意之所之,自由无碍,有如一个小孩走入大丛林一般,时或停步仰望星月,俯看虫花。我不管别人说什么,而在这探险程序中也没有预定的目的地。没有预定的游程,不受规定的向导之限制。如此游历,自有价值,因为如果我要游荡,我便独自游荡。我可以每日行卅里,或随意停止,因为我素来喜欢顺从自己的本能——所谓任意而行,尤喜欢自行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美,什么不是。我喜欢自己所发现的好东西,而不愿意人家指出来的。我已得到极大的开心乐事,即是发现好些个被人遗忘的著者而恢复其声誉。现在我心里想着精选三百首最好的诗,皆是中国戏剧和小说里人所遗忘和不垂意之作,而非由唐诗中选出。每天早晨,我一觉醒来,便感觉着有无限无疆的探险富地在我前头。大概是牛顿在身死之前曾说过,他自觉很像一个童子在海边嬉戏,而知识世界在他前头的有如大海之渺茫无垠。在八岁时,塾师尝批我的文章云:“大蛇过田陌。”他的意思以为我辞不达意。而我即对云:“小蚓度沙漠。”我就是那小蚓,到现在我仍然蠕蠕然在沙漠上爬动不已,但已进步到现在的程度也不禁沾沾自喜了。
我不知道这探险的路程将来直引我到哪里去。谁能逆料我将来结果不至成为一个共产主义的哲学家呢?然而我决不至流为一个共产主义的行动者。思想生活和行动生活是大相径庭的。有些人确能兼而为之,但两者精神上是相反的。世界上只有两种动物,一是管自己的事的,一是管人家的事的。前者属于吃植物的,如牛羊及思想的人是;后者属于肉食者,如鹰虎及行动的人是。其一是处置观念的;其他是处置别人的:我常常钦羡我的同事们——行政和执行的奇才,他们会管别人的事而以管别人的为自己一生的大志。我总不感到那有什么趣。是故,我永不能成为一个行动的人,因为行动之意义是要在团体内工作,而我则对于同人之尊敬心过甚至不能号令他们必要怎样做、怎样做也。我甚至不能用严厉的辞令和摆尊严的架子以威喝申斥我的仆人。我又怎能组织暴动,或指挥罢工,或运动正式的政治革命呢?我常赞扬一般革命者和官吏,以他们能造成几件关于别人行动的报告,及通过几许议案叫人民要做什么,或阻止人民做什么。他们又能够令从事搜讨研究工作的科学家依时到实验室,每晨到时必要签名于簿子上,由此可令百分之七十五分三的效率增加到九十五分五。这种办法,我总觉得有点怪。为什么科学家每晨到办公室去必要签到呢?这样增高的“效率”将可以帮助他们呈出多些重要的发明吗?我以为在一个科学研究馆中实施科学的管理法实是一个笑话,是名辞上的矛盾。同样,我也鄙屑一般大学教授之答复来函过于快捷。个人的生命究竟对于我自己是最要不过的。也许在本性上,如果不是在确信上,我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或道家。
现在我只有一种兴趣,即是要知道人生多些——已往的和现在此处的,兼要写人生——多半在脾气发作之时,或发奇痒、或觉有趣、或起愤怒、或有厌恶。我不为现在,甚至不为将来而忧虑,且确然没有什么大志愿,甚至不立志为著名的作者。其实,我怨恨成名,如果这名誉足以搅乱我现在生命之程序。我现在已是很快乐的了,不愿再为快乐些。我所要的只是些少现金致令我能够到处飘泊,多得自由、多买书籍、多到地方、多游名山——偕着几个好朋友去。
我自知自己的短处,而且短处甚多,一般批评我的人大可以不必多说了。在中国有许多很为厉害的、义务监察的批评家,这是虚夸的宋儒之遗裔而穿上现代衣服的。他们之批评人不是以不幸的有极的人为标准,而却以一个完善的圣人为标准。至少至少,我不是懒惰而向以忠诚处身立世的。
载第19期(1936年12月5日出版)
我和言论界的因缘
……
柳亚子
丹林兄替《逸经》拉稿子,要我写文章,而且出了一个题目,是《从事新闻界之经过》。我觉得这题目不甚高明,就给他改了一下,写成此篇。
公元一九〇三年(清光绪廿九年),我第一次到上海,进了爱国学社。这时候,和章太炎、邹威丹两位先生很接近。在阴历五月中旬,《新闻报》登了一篇《革命驳议》,太炎先生便写《驳革命驳议》,来反驳它,开了一个头,他不高兴写了,叫我续下去。我续了一段,同邑蔡冶民先生也续了一段,末尾是威丹先生加上去的。我的一段,是关于菲律宾独立的问题。大概是如此:《新闻报》主笔说,二十世纪,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时候菲律宾大总统阿圭拉度将军刚刚失败,他就拿来做一个例子。而我的驳论,是失败者成功之母,菲律宾虽然失败,将来一定会成功的。这篇文章在《苏报》上发表,这便是我和言论界第一次的因缘。
爱国学社解散以后,我还乡间住了半年,闲得不耐烦,就去同里自治学社念书。又搅了一年多,好像一九〇五年(清光绪三十一年)吧,我们就发起了一个自治学社学生自治会,办成了一个《自治报》,是用钢笔蜡纸搅的,我们自己写,自己印,自己分送,每一星期出版一次。后来,把《自治报》改成了《复报》。到一九〇六年(清光绪三十二年),我脱离了自治学社,到上海健行公学教书,把学生自治会改做青年自治会,俨然是中国同盟会的预备军。一方面,把《复报》从钢笔版改成铅印,从周刊改成月刊,从单张改成单行本,在日本东京出版,居然成为了《民报》的小卫星呢!
一九〇七年(清光绪三十三年)起,《复报》出到了十一期而停版了。我又在家中闲住,一住便是五年。直到一九一一年(清宣统三年)秋天,再来上海。经过了武昌革命和上海光复,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一月,去南京大总统府当了三天的秘书,抱病而还。这时候,我是无聊极了,就有南社老友邹亚云、陈布雷介绍我进《天铎报》,笔名青兕,论文是犀利无前。反对南北议和,反对袁世凯,和《民立报》、《大共和报》都曾大开笔战过。后来,从《天铎》转到《民声》,又从《民声》转到《太平洋》。在《民声》时做随笔式的文章,叫“上天下地”栏,还不免使酒骂座的习气。在《太平洋》专编文艺,替冯春航捧扬,一面和曼殊、楚伦大吃其花酒。曼殊常叫的倌人是花雪南,楚伧是杨兰春,我却是张娟娟。记得有一首绝句道:“花底妆成张丽华,相逢沦落各天涯。妇人醇酒寻常事,谁把钧天醉赵家?”颇有英雄末路的感慨。到这一年的暑天,浩然有归志,从此可说是实际上脱离了言论界了。
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八月,齐卢战争,我又来上海避难。邵力子主编《民国日报》,时常请我代做批评,好像是票友客串,却未下海。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春夏之交,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要在上海办党报,定名《国民日报》,委任张静江先生做总经理,张廷灏副之;我做总编辑,沈雁冰副之。结果,静江先生在广州不来,我又灰心国事,躲在乡下,而《国民日报》在法租界的照会,公董局始终不肯发出,成了僵局。直到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国民革命军占领上海,上海一部分同志盘下了《神州日报》馆的机器,《国民日报》始正式成立,好像总编辑还是用我的名义,而我却始终未曾出山。结果,《国民日报》出版不到几天,清党事起,全局推翻,我的总编辑头衔也从此取消了。
自此以后,我除了零星投稿以外,再也没有和言论界发生整个的关系过,所供是实。
完了。
一九三六一三〇夜,上海
载第1期(1936年3月5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