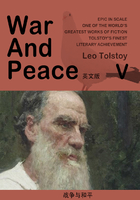汽车站到了,场长伸出满是老茧的手用力握了握痕的手,口里说出一句奇怪的客气话:“对不起啊,平时对你照顾不周,多多原谅吧。”
痕当时心里想,场长还不到60岁,就已经老糊涂了,说起话来颠三倒四的。他又不是去送死,干吗这么伤感?早知要伤感,平日里那些个尖酸,那些个疙疙瘩瘩的阴暗情绪为什么不收敛一下,这样痕对他的怨恨也小些。现在痕不过出一下门,他就小题大做起来,完全是做人前后不一致,莫名其妙。这样一想,刚才对场长的同情又消失了,只觉得像他这样素质低、没头没脑的人实在讨厌。痕冷淡地干笑了两声,场长就转身往回走了。痕打量着他的背影,感到这人从头到脚都是一副蠢相。
痕万万没想到场长会帮他买软卧车厢的车票。当他在验票处从大信封里拿出车票时,连手都在微微发抖。以前他也出差,场里总是只给买硬座,对他来说坐车是件苦差,可是习惯了也就好了。痕甚至有点喜欢出差,因为场长总是慷慨地补给他津贴。按场长的逻辑,车的等次差点,辛苦一点没关系,只要经济上加以补偿,工作起来就会更有劲头。一直到了软卧车厢,在自己的包厢里做梦似的放好了行李,坐在自己的铺位上,痕还想不通场长的这种安排。他将信封里的东西全倒出来,发现都是钱,有一千多块,远远超出了他这趟出差的费用。可是里面没有购买饲料的合同!场长一定是忘记了。车已经徐徐启动了,怎么办?痕急傻了,在包厢里踱来踱去。他无意中瞥了一眼手中的火车票,发现上面是一个陌生的地名,根本不是场长告诉他的“鱼县”。鱼县是痕过去常去买饲料的地方。他连忙从旅行包里找出地图,寻找这个名叫“坤市”的地方,一边找一边冷汗就从额头上冒出来了。他用力瞪着那些蚂蚁般大小的地名,眼珠都鼓痛了,还是没找到坤市。他只好拿了车票去问列车员,那列车员告诉他坤市在黑龙江省,是个很小的新镇,地图上一般没有标示,位置在边境上。痕失魂落魄地回到包厢里,暖气的热浪袭击着他,只觉得全身都被汗水湿透了。总不会是场长用这种方法来解雇他吧?如果他要解雇他,完全可以直说,何必用这种奇怪的手段。场长知道他的性情,也知道他对旅游毫无兴致,所以要是场长解雇他的话,他绝不会因为场长让他旅游、坐软卧而减轻对他的憎恨,这一点他必定也考虑到了的。冷静地看,那种可能性还是极小的。还是回到第一个猜想吧,场长忘了给他合同了。他都联系好了,这回是去一个新地方购买饲料,场长担心他完成不好任务,一直忧虑在心,就把合同的事给忘了。痕回忆起在去汽车站的那10分钟路程里,场长一言不发,恐怕就是在担心他买不到好饲料。如今做买卖到处诈骗成风,十次里头有六次不上当就算是非常老练精明的人了,痕过去也常上当,奸商的手法防不胜防。再说场长本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从不与自己的下属讨论工作上的事,当时痕就是冲他这一点才留在鸡场里的,痕最讨厌与人讨论。这样一想,痕又稍稍放下心来,决定把这趟车坐到目的地,一到坤市就给场长打电话,问清购饲料的具体地点,让场长把合同寄来,合同未到之前自己先到饲料厂去调查一下商品的质量。这一惊一乍的,把痕的情绪搞得很消沉,又像从前一样在心里骂起场长来。痕活了四十多年,从未见过比场长更为独断专行的人,他同场里的任何一名雇员都不接近,如果雇员做错了事,他总是毫无例外地破口大骂,什么让人脸红的话都骂得出来,甚至叫人“滚蛋”。痕已经看见他赶跑了好几个人,有一回竟然是用竹扫帚将一名雇员打出去的。那人吓得不敢回来取自己的衣物,可又不甘心,只好藏在离鸡场一里外的灌木丛里等。后来痕从那里经过,他就一把拖住他苦苦哀求,痕只好夜里乘人不注意将他的东西收拾好,挑了一担奔往他躲藏的处所。后来回想这事痕总觉得有点窝心。平时场长骂他时,他心里从来是不服的,等场长走了,他就用最毒的字眼诅咒他。他知道场长不会把他怎么样,当然他也留心着自己的行为不要过分。那么场长刚才为什么向自己道歉呢?痕心里的怀疑又像虫子一样蠕动起来。
后来列车长就来了。列车长进来后就坐在对面的铺位上,开始只是闷头抽烟,时不时地看表。痕的注意力被他吸引过去,心里感到纳闷,这位列车长,现在正是他当班的时候,他怎么会这么悠闲呢?在痕的印象里,列车长们总是有很多大小事务要处理,忙得不得了。
“有点寂寞吧?”他忽然开口了。
痕看清了一张乡下人的脸,很健康,但似乎常年被日晒雨淋,这与他的列车长的身份是很不相称的,他看上去更像刚刚下地回来的农民,他身上有菜土的气息。
“我也是很寂寞啊。这几天我老想,我为什么还要出车呢?莫非还有什么好奇心?车上每天都有生命危险,这些旅客全是些流氓恶棍,有的还是杀人犯,这种事我见得多了。您知道他们为什么出来旅行吗?就因为怕被别人所杀!所以实话告诉您吧,铁路这一行我早干腻了,这算什么工作呢?夜里提心吊胆,无法入睡,总在策划对付这些恶棍的方案!您一定以为我有五十多岁了吧,其实我才三十八!我只要一上车就把地上的事忘得干干净净,成天像气球一样飘来飘去,难受得要死!”
他莫名其妙地发作了这一通之后,就指着窗外远方的一栋建筑,告诉痕说,那是一家县银行,前不久蒙受了重大的损失,作案的手法再简单不过了。痕一开始并没有心思听这种闲谈,他的情绪还沉浸在刚才那场惊吓的余波里。可是列车长只顾说下去,似乎对那个身为银行业务员的盗窃者十分佩服、欣赏,又似乎还有更深刻的看法,因而毫不在意自己所说的具体情节似的。因为痕注意到有好几次,列车长将银行说成了邮局。痕一下子对这个人说话的方式产生了兴趣,不由自主地加入了谈话。一会儿过去,连他自己也觉得奇怪,他很快忘了刚才那场惊吓。再过了一会儿,痕又感到了厌倦,列车长根本不像个见多识广的人,除了口音掺杂之外,一点都看不出他到过很多地方。他所谈的事都是些老套,大同小异,听多了令人反胃。现在他给痕的印象是一个头脑狭隘的人,周围的事物变化对他毫无影响,他的职业也改变不了他,他的职业只是更加深了他的偏执。然而谈话持续到夜里,当痕面对列车长时,一种幻觉产生了:似乎这位列车长并不是个简单的乡下汉子,他的外表有种蒙蔽作用,正如他说的话有种欺骗性一样。他之所以反复地说这些乏味的故事,是因为他自己也认为这些故事本身毫无意义,而他要表达的意思深埋在这些乏味的故事底下,因为藏得太深,他要挖出来也不可能了。可是除了这些故事,他又想不出别的法子来表达,他就只好一遍又一遍徒劳地操练了。痕注意到,列车长说话南腔北调的,从他的语音里,还不时透出痕自己家乡的尾音来,给了痕很熟悉的印象。莫非这汉子从前是痕的家乡人,后来走南闯北才将语音弄得复杂起来了?痕还有一件想不通的事:这么一车人,列车长为什么独独选中了自己来聊天呢?
缩在毛毯里,痕将发生过的事的细节想了又想,那些零碎的片断就慢慢地被他连了起来,逐渐形成了一张网,他无法不相信,但又不得不猜疑。痕再次用包厢里反正有三个人这个事实来安慰自己,他不能相信场长会陷害他,他多年的经验一再告诉他:场长是个十分孤独的人,与外界几乎没有什么联系,成天只知道埋在养鸡场的事务里,这样一个人,怎么会认识这列火车上的列车长,从而联合起来整治他呢?这种想法太荒唐了,太神经质了。天怎么还不亮呢?痕又一次想看表。
“喂,您有火吗?”他用脚推了推乘警。
“有火有什么用?真是莫名其妙!”乘警不高兴地说。
“我想看看表,几点钟了啊?”
“您就待着吧,知道了几点钟又有什么用!反正这车一时半时不会开了。”
“我们是停在河上吧?”
“屁!这里是隧道,要不哪能这么静!”
“隧道里怎么连盏灯也没有?”
“这个隧道里从来没有灯。喂,您到底要啰唆到什么时候去?要不您把毯子还给我,我躺到我铺上去。真不知好歹!”他气呼呼地闭了嘴。
痕藏在心里头的那一点希望一下子破灭了。原来这里是隧道,这就是说,只要车不开,天就亮不了。还是冷静点吧,他何必急着要天亮呢?他虽然肚子有点饿,总饿不死的,这两个人的肚子也总会饿的,他们总不会一直睡下去的。只是把暖气关掉这一招实在是太恶毒了,他已经付了钱,买了这么贵的票来坐车,列车长他们这样做是犯法的,他等这两个人起来后一定要去提抗议。他要向那些人说,这样对待一个旅客简直是欺诈行为,而且还把包厢的门闩上,又不让开灯,如果躺在里面的不是他,而是一个,比如说,一个年老体弱者,这种行为不就类似于谋害吗?痕心里的愤怒越来越厉害,也不知道害怕了,一冲动就跳下铺,鞋也不穿,用两只拳头去用力打门,口里还乱七八糟地发出些吼声。他要发疯了。
在他吼叫的一个间隙里,他突然听见乘警的声音:
“门根本就没关,把插销拿开就是。”
他摸索了一阵,果然找到了插销,门“吱呀”一声开了。他在门外摸到电灯的开关,发现那开关本来就开着的。再看车厢两头,到处都是黑洞洞的,连一盏小灯都没有。他转回来问乘警到底出了什么事,乘警说是为了节约能源,又说他如果不想再躺在铺上,他可要占掉他的位置了,不过他还是劝他回铺上来,等会儿会冷得受不了的。站了一会儿,痕真的冷得受不了了。他趿着鞋摸黑走到那头的餐车里,餐车也是冷冰冰的,异样的寂静令人胆寒。他连忙退了出来,沿狭窄的小道回包厢去。他刚走到半路,一个胖大的女人将他吓了一跳,腿一软差点摔倒。那女人堵住了过道,痕过不去,他只好愣在原地,闻着女人身上的鱼腥味(他猜她是厨房里的勤杂工)。
“多么冷啊。”女人说,她的声音很好听。“我是一个很漂亮的姑娘,可惜您现在看不见我。我有点难受,夜里出来走一走,要不是车上关了暖气,您就碰不到我了,白天我是不走出厨房的。您喜欢漂亮的姑娘吗?我看您一定是个单身汉,您走来走去的,一定是想打猎吧?像我这样的好货色可不是随便碰得到的。啊,要是现在有灯光的话您就可以看见我了,只是我本人倒不怎么喜欢灯光,我喜欢躲在黑暗的地方,我太漂亮了,我怕车上的男人纠缠我。怎么,您受到我的诱惑了吧?这种地方最容易产生冲动,尤其像您这样的单身汉,是绝对抗拒不了自己的欲望的。”她似乎在那里笑。
痕不由自主地伸出双手,那女人立刻捉住他的手捂在怀里。女人的手掌很粗糙,很热和,她的怀里也是热气腾腾的,痕将冻僵了的身体朝她凑过去。女人很高,痕的头只齐到她的胸口,他将脸贴着她的乳房,立刻就不再发抖了。女人的手来回抚摩着他的头,很温柔地轻笑着。
“您真是一座火山。”痕喃喃地说,似乎自己心里所有的重压都在这一刻化解了似的。
“来吧,来吧……”女人一边轻轻地念叨一边将痕干瘦的身子抱了起来,用力从过道挤过去,挤得铁皮墙都嘎嘎作响——她实在太胖了。
他们似乎穿过了厨房,因为痕闻到了油烟味、食品的各种香味等,最后痕被放在她的一张椅子上了。女人说这是她的工作间兼储藏室。她在他面前窸窸窣窣地脱衣服。一离开女人,痕又冷得发抖,房间里腐烂的白菜味儿熏得他脑袋发晕,只想呕吐。可是女人已经脱完衣服了,一把将痕抱过去,又帮他脱起来。痕心里想自己一定是冻得嘴唇发青了,他倒希望快点脱完,与这个火炉似的胖女人缠在一起,说不定自己也会暖和起来。现在他已经脱光了,进入了女人的身体。他立刻发热了。他仿佛睡在一只又大又暖和的船里面,舒服得要进入梦乡了。女人轻轻地摇晃着他,两只粗糙的大手令他很舒服地抚弄着他的腰和屁股,使痕产生一种在黑洞洞的深海里游泳的感觉。现在他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求了。这意外的艳遇似乎将他心里的那些焦虑全都融化了,此刻他甚至连自己身处何方都不愿搞清楚了。
不知过了多久,女人忽然在他的瘦屁股上用力拍了一下,大声号哭起来:
“哎呀!空虚呀!真是难受呀!我一直在这里等,等一个人来把我塞得满满的,我等了又等,以为等到了,没想到还是空空落落。我到底是怎么啦?啊呀,我要死了!”
她满脸的眼泪鼻涕,擦在痕的脖子上溜溜滑滑的,很不好受。痕像一只瘦螃蟹一样缓缓地从女人身上移开,到地板上去找自己的衣服。他找了好久才找到,冷得不停地打喷嚏。女人一直躺在地板上不起来,一阵一阵地猛烈啜泣。痕想,自己反正没有办法安慰她了,只有赶快穿好衣服逃跑。他把衣服往身上一套,提起裤子就准备走。地板上的女人一把扯住他的腿不放。
“哪里去?”她止住啜泣,声音变得阴险起来,“占了便宜就走吗?”
痕站住不动了,一边系着裤子的皮带。
“坐下!”女人吼道。
他蹲了下来,被女人一把搂过去,坐在了她的大腿上。那地方倒也不错,很软和。女人背靠着墙,用一只手掌轻轻地拍打着他的背脊,就好像他是一个婴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