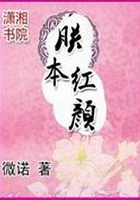痕紧紧地跟上他,担心在黑暗中要是离得太远就看不见他了。痕知道傻大姐就潜伏在去餐厅的过道里,她会如何对待这个老头呢?老头并不想摆脱痕,好像还有点高兴,不时停下来等痕离他更近一点。刚一进过道那女人庞大的身影就出现了,后来的情形与痕预料的相反,不是女人将这老头掳去,反而是老头主动袭击她。黑暗里痕不断听到拳头打在肥肉上发出的响声,夹杂了女人的尖叫和哭声。到后来力大无比的老头就把女人踩在了脚下,他在她肚子上用力跳,而女人的号啕惊天动地。老头打累了,还不甘休,又一拳打破了过道里的玻璃窗,玻璃碎落下来,掉在女人身上,女人一滚,大概玻璃扎进了肉里,又发出恐怖的叫声。这时痕走过去,想扶起受了伤的女人,他的手触到女人的身体,裙子的前胸一片湿漉漉的,大约是出的血。痕不由得战栗起来。这时那老头已经走掉了,痕用尽全力将大声呻吟的女人扶起来,可是傻大姐似乎并不高兴他的帮忙,刚走了两步,她就甩脱他,赖在地上不起来了,口里大声呼痛。过道十分狭窄,痕被卡住动不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法再次将她扶起,他自己的腰反倒被这一大团肉压伤了。这一番挣扎弄得他怒火直冒,可是女人不但不合作,还口里哼哼地要他“滚开”。痕绊倒在女人身上,自己的手也被玻璃扎了一下,火辣辣的。他想站起来,傻大姐偏不让,用两条腿紧紧地夹住他。这时右边的壁缝里忽然射出一道光,窄窄的一条射在对面窗户上。傻大姐似乎吃了一惊,连忙放开了痕,痕跳起来就往餐厅那头跑。
“列车长等着您去见他呢!”女人在身后喊道。
他觉得自己脚下生风似的,熟门熟路地就摸到了厨房,一路摸过去,到了一间大约是放餐具的房间,左边有个小门,灯光就是从那里透出来的。门的上半部是玻璃格子,痕对直望过去,看见列车长和刚才那老头坐在一张窄床上谈话,老头背对着门,只看见他后脑勺上稀疏的白发。痕迟疑着没有推门,那两个人说话的声音很大,显然都没有听见他的脚步声。
“那家伙还在吧?”列车长问。
“怎么会不在?刚才还和我在一起呢,我请他看了一场好戏。”老头夸张地说,耸了耸肩。
列车长瞪着两只无神的眼睛,大手笨拙地伸进裤袋里去掏东西,掏了半天,掏出一条脏兮兮的手绢,就用手绢捂着鼻子打喷嚏,打个不停,脸都憋得发紫了。这时痕看清了,房里点的是一盏煤气灯,那灯挂在屋当中,里面的气体发出不祥的“噗噗”的声音。列车长的喷嚏终于打完了,眼泪汪汪的,痕觉得他瘦了很多,蓬头垢面的,一副可怜相。这样的人怎么谈得上要来收拾自己呢?不过人心叵测呀。
“回忆吧,回忆美丽的往事吧。”列车长伤心地说,眼珠瞪着面前的墙发了愣。老头怜悯地看着列车长,伸出一只手在他背上摩挲着,口里在念叨:“不要紧,不要紧……”就像在安慰遭到了重大打击的人一样。不过他的安慰并没起作用,列车长像石头似的一动不动,房里那盏煤气灯的声音响得有点吓人。这种情形让痕觉得自己此刻推门进去很不合时宜,但是他怎能放过这个机会呢?在这列火车上,除了列车长,他再也没有别的人可找了,毕竟这个汉子同他聊了那么久的天,一点都没表现出敌意;再说他是一车之长,是这个车上最有权势的人,也是最知情的,万一车上要发生什么事的话,没有人会比他更清楚。他心里的疑团必须找列车长解开,越早解开对他本人越好,这一点是肯定的。这时痕又有点后悔,昨天自己为什么不对列车长更亲切友好一点呢?还是自己那该死的本性作怪。细细一想,活了这么多年,从来不曾交一个知心朋友,不论和谁打交道他总是保持那种距离感,外人看来必定是冷冰冰的。
痕打定了主意推门进去时,那老头便回过头来了。痕口呆目瞪地发现,老头竟是鸡场里的清洁工,投毒的那一位。他不是三个月以前就辞职了吗?当时场长还说他是回老家去了呢!
“您好呀,老单,什么时候出来的呀?”痕走上前去与他打招呼。
他说了这话之后,看见列车长与老单迅速地交换了一下眼色。
“我在这列火车上干了三个月了。”老单挺直了身子一本正经地说。
“原来找到了新的工作,恭喜您呀。”痕的话里透出讨好的成分,自己也感到吃惊。
“根本不是找到了新的工作,”老单厌烦地挥了一下手,“是鸡场的场长将我骗上火车的。我反正老了,也就随遇而安了。您坐车去哪里?”
痕心中一惊,脸上变了色,脑子里轰轰作响起来。过了一会儿才如梦初醒。“我出差,去买饲料……不过这种事谁又有把握?我很怀疑……场长是一个捉摸不透的人。不管他,出来好,扩大眼界,鸡场里太闭塞了。”他乱七八糟地说出这些话,更加不安了。
“您怀疑什么呢?怀疑是好事,年轻人就该怀疑。”老单说话时又对列车长使了个眼色,痕觉得这两个人脸上的表情都很淫荡。
他俩因为痕的在场明显地活跃了起来。列车长的身子往后靠在墙上,他的脸藏在阴影里,痕看见他从那个地方死死地盯着自己,那种眼光完全不同于从前的冷漠。
“怀疑好,什么事都不要轻信,我原先就想和您说这句话,可惜您年轻气盛,什么都听不进去。”老单还在说。
痕像犯人一样站在他俩面前,准备好的一肚子话全忘得干干净净了,中了圈套的感觉又回到他身上。面前这两个人是一堵墙。列车长刚刚还那么软弱,现在一下子就硬起来了,他那种样子似乎像举着鞭子将自己往圈套里赶。所以痕根本不敢同他对视。
这样站了一会儿,听见列车长站起身来,伸手将他身后的另一扇小门打开了。从这扇门望过去,痕看见一排排放蔬菜的木格子,可能正是他和傻大姐待过的那间房。列车长从小门走进那间房,就反手将门关上了。听见那边房里在低声说话,一会儿就传出了女人的号啕大哭,傻大姐这一回哭得更凄惨,撕心裂肺似的。痕一脚踢开门走进去,看见列车长正挥起一把铁锤朝女人砸过来,铁锤砸在女人的大腿上,甚至听见骨头折断的响声。列车长抬头看见痕,立刻扔了锤子,从他身边擦过,回到自己房里,将门用力关上。痕和女人又处在完全的黑暗中了。女人躺在地上,那一大堆身躯抽搐着,痛得不停地叫喊。
痕蹲在她旁边,抚摸着她受伤的腿,发现她全身冰凉,也许是失血过多吧。列车长的凶暴把痕都吓坏了。痕一边安慰她一边记起,刚才自己又忘了看她的脸,她到底有一张什么样的脸呢?这个可怜的女人,为什么会受到他们这样的非人的折磨呢?
“啊,我要死了!我活不成了!”女人的双手在黑暗里乱抓。
痕竭力想安慰她,却被她扇了一个耳光,脸上麻辣火烧的。痕想,既然她还有这么大的力气来打人,那她的伤就不要紧。于是他移到角落里倚墙站住。隔壁的两人在说话,门关得死死的,也许又从那边闩上了。他听见列车长在那边房里喊他,开始他还以为是幻觉,仔细听真是喊他,列车长还跺着脚在那里大发雷霆。这时傻大姐停止了哭叫,小声对痕说:“啊,不要去,不要去!到我身边来呀,小猴子,我不会再打您了。”痕回到她身边后,她就轻轻地呻吟着,一边轻轻地告诉他:
“我可不是什么娇嫩的姑娘,这点伤,哼,难不倒我。您不要怜悯我,这种事常发生,他们脾气都很大。我还从来没见过您这样的,您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那一天我从厨房那里看到您,我简直抑制不住自己。我躲在这里想呀想的,我想,也许您是一个幽灵?”她的冰冷的大手在痕脸上摸来摸去的,弄得他很不舒服。
列车长在隔壁叫得更响了,好像还将什么东西砸在地上,老单也帮着喊痕的名字。他们为什么自己不过来呢?痕稍微一动,女人就按住他。
“不要去,您的身体太单薄了,我真为您担心啊。您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的?”
女人的最后这句话激怒了痕,他心里一股无名火直冒。
“我落到什么地步啦?您说说看。莫非遭难的是我吗?啊?看看您自己吧,被人打伤,躺在地上没人管,您怎么还说这种没有自知之明的话呢?这种话如果是,比如说,我们场长说的,倒还可以理解,因为他大脑迟钝,什么事都搞不清……”痕突然住了嘴,因为他发现自己说得太多了,心里害怕起来。
“您还在对鸡场里的事耿耿于怀呀!”女人说起话来好像痛苦全消失了,“喂,您告诉我,他们说您是因为挪用公款被赶出来的,这是真的吗?这事真有意思啊。”
傻大姐竟然坐了起来,十分兴奋似的,她拉过痕的手放在自己的两只乳房中间,像麻雀一样叽叽喳喳起来。她反复地询问痕,怎么会有勇气做出那种事来,做了那种事之后又怎么还能出来旅游,场长对他的处罚到底是重还是轻,他自己到底是像别人说的那样是一名恶棍,还是正派人的一念之差?她身上散发出血腥的味道,体内又渐渐地恢复了热力。但痕此刻一点都感觉不到她的诱惑,不论她如何暗示都没有用,他只觉得厌恶,就像喝汤喝进去一只苍蝇的那种感觉。列车长与老单还在那边叫他的名字,他们的声音使得痕万念俱灰。
“您,怎么会只有一边脸的?”他恶毒地对女人说。
“嗬,您并不介意嘛,谁都有可能遇到这种事的。那边那两个家伙想掌握您的行动,他们不高兴您在我这里待得太久。这里有西红柿,您一定口渴了吧?”
女人和痕一人吃了一个西红柿,她又说她在架子后面藏了一只烤鸡,让痕扶她站起来,她好去取。她瘸着腿走到那边翻了一阵,木架忽然倒了下来,腐烂的蔬菜弄了痕一身,气味令人作呕。痕怀疑是女人故意弄倒的。
“坐下来吃鸡吧,不过要轻轻地,弄不好就会被隔壁那两个人抢了去。”女人对他耳语道,顺手递给他一只鸡腿。
痕这么久没沾荤腥,也顾不得脏,就大口吃起来了。女人自己也吃,果然轻轻地嚼,生怕弄出声音来。一会儿两人就把一只鸡吃光了。女人又从什么地方摸出一瓶啤酒,两人你一口我一口地喝了起来。痕虽然情绪很低落,但毕竟吃饱了肚子,也就没有那么难受了。那边那两个人也沉默了,可能已经走了也不一定。
“这种日子,不是也很令人满意吗?”女人口里还塞着鸡肉,说话含糊不清的。
痕脑子里乱极了,他不愿和女人讲话,他想走。他走到哪里去呢?老单就如潜伏在列车上的一条毒蛇,不论他走到哪里他都会悄悄地跟在他后面潜行,到时候就给他来那致命的一下。老单是不是场长派来的呢?如果不是,那他就只不过是在造谣,败坏他的名誉罢了。因为他自己已落到了底层,不甘心,还要把他痕拉下水。假如是这种情况,痕就用不着怕他。万一真是场长派来的呢?投毒的事又如何解释呢?他打了一个饱嗝,那饱嗝里头不但有鸡的味儿,也有烂白菜的味儿,那鸡原先是放在烂白菜堆里的,刚才那木架一倒,弄得他手上也沾满了脏兮兮的汁液,又没有擦一擦就去抓鸡吃,所以脏东西都吃进肚子里面去了。痕惊异于自己竟然能在污秽中待了这么久,还将污秽吃了下去,这是从前想都不敢想的。莫非他已经堕落得不成样子了吗?要真是这样,说他挪用公款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一边这样想,一边就有股热力往上冲,这是上车以来还不曾有过的。也许他真应该自暴自弃?他到底在坚守些什么东西啊?一个鸡场的保管员,被老板解雇了,却还不肯随遇而安!所有他想追问的那些东西都已经不存在了,刚才列车长的态度已经表明了这一点。这是不是说,他和傻大姐是一类人?不,也不是,傻大姐也分明看不起他,只是因为无人可交往,女人才缠上他,这种纠缠有很大的利用的成分。可以说,傻大姐将他抓来给自己垫背。话虽这样说,痕还是觉得自己被傻大姐利用是件好事,他在这里是如此的孤立,无人理睬,如果跟着这个女人的话,自己会慢慢搞清内情的,这也是他巴不得的事,何况这女人还有她温柔的一面,并不完全是母夜叉。根据痕多年的经验,很多事都是由她这样的小人物成就的。
这时女人用油腻腻的手在他脸上摸了摸,那手热得像火炭一样。然后她就坐在地上用裙子擦手,似乎擦得很仔细,就像很爱卫生似的。
“给我讲讲您挪用公款的事吧。”
“我并没有做那件事,为什么您要这样认定?我是养鸡场的保管员,场长派我来出差,亲自为我买好车票,我是去购买鸡饲料的。”
“当然,开始都是很正常的,我当年也经历了这些很正常的事,后来我就成了这车上厨房的一名帮工,这一点都不奇怪,只是来这里之前,我弄坏了一边脸。”
女人的语调里透出对痕的理解,还有淡淡的伤感。
“根本不是同一回事!”痕提高了嗓门。
但是他也想不出他和女人的不同在哪里,女人又是如何到这列车上来的。他说了这句话之后,女人就把他拖到她的身边,用手臂搂紧他,让他的脸紧贴她那暖烘烘的乳房,用另一只手揉搓着他的胸膛,轻轻地安慰他:
“不要急躁,慢慢来,日子还长着啊。那么多年了,我是怎么过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