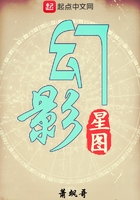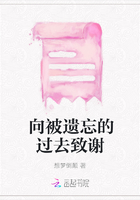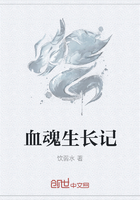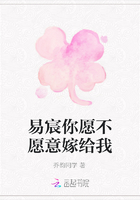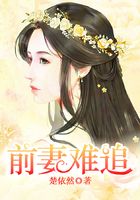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不不,严格说来,在我工作之前,医院已经有人在叫他疯子了。
关于他疯子的来历,说法不一。有人说,他从来都着对襟中装,不穿医院统一的工作服;有人说,他看病人之前,都要先喝一口白酒,才能开出处方;也有人说,他给病人开出的处方,药量之大,让其他中医心惊不已;更离奇的说法是,他常常无缘无故地痛打老婆,还让老婆写保证书;稍微有点让人信实的说法是,他在全县的中医学习班上,做了反对中西医结合的发言,被局长骂了一通等。正式参加工作之后,在一次酒后,从医院办公室仇国平主任的嘴里,我听到了最原始的说法。
八十年代末,华东地区爆发甲肝,不懂医理的百姓,把板蓝根冲剂当作防治甲肝的灵药,大量抢购,医院发霉的存货都卖脱销了,连中药房药库的板蓝根药草,都被百姓抢购一空。陈院长立刻组织医院的采购人员,分成三个小组,到各地采购板蓝根。这个时候,他得知了消息,立刻来找院长。他是从三楼一口气跑到五楼的,平素刻板的头发乱着,表情气急,口气强硬:“陈院长,我叫你一声院长,我是学中医的,你也是学医的,你心里应该懂得,这个……板蓝根从药理上,根本没有防治肝炎的作用。老百姓不懂,在以讹传讹,我们是懂医的人,不应该推波助澜啊。陈院长,我叫你一声院长,我建议在医院门口贴个告示,把其中的道理告诉老百姓,省得老百姓瞎害怕,也省得老百姓瞎糟铜钱。”
陈德兴院长眼睛直定定地杵着他,嘴张了又合,合了又张,那句话没有出声,是仇主任后来照着嘴型猜出来的:“疯子。”
我生平第一次跟他面对面的接触,是在我确定进传染科之后。
那是一九九〇年代初,传染科还躲在医院的西北角落,一个独门独户的院子。据方志记载,这里原来是大户人家的后花园,四周的病房原先是花匠们住的地方,理由是,大门的一侧,有座老式水塔,青砖砌成的,是浇灌花卉用的。院子中间,栽种着很多不知名的小花小树,密栽密长。春天一来,花红树绿,心情随花木的开放而奔放,舒畅。
当时的医学界,对病毒性肝炎所知不多。肝炎仅仅分为甲肝、乙肝、非甲非乙型三类,化验也只能做到黄疸指数跟谷丙转氨酶,临床痊愈的指标就是它们。很多病人经过治疗之后,谷丙转氨酶始终无法正常,总是比正常指数超过一点点,临床习惯性地称为小谷丙。
记得是那年春天,一个鲜亮的日子,我跟着柴元方主任查房,面对众多病人的小谷丙,柴主任面呈无奈,我当然更没办法,就听到住院将近三个月的高生平说:“柴主任,能不能开点中药让我们试试?”
柴主任立刻异议:“我这里是西医,没有这样的先例,你想吃中药,出院再吃。”
高生平,二十五岁,乙肝,在食品公司杀猪,是街上有名的城痞子。“出院吃药谁给我报销啊。”
老农民周兆庚说话了:“听说储名医就在你们医院,请他来看看,可能会有办法呢。”
柴主任生气了:“你是医生,还是我是医生?听你的,还是听我的?万一吃中药出了事故,谁负责呢?”
又是高生平:“吃中药我签字,吃死了不要你偿命。”
柴主任很无奈,回到办公室,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生了半天闷气:“于医师啊,写个会诊单,去请储伯达来会个诊。”
“陈伯达?”我拿着病历的手一滑,差点掉地上。
“是储伯达,喏,就是储疯子。”柴主任依然阴着脸,“对了,想吃中药的一律签字啊。”说完出了办公室大门,闷气还留在屋里。
中医科不设病区,只有门诊。我拿着会诊单来到门诊,才要进门,忽然从医院大门的方向,敲锣打鼓涌来一群人,气势像极了古代行军的方阵。走在最前头的,拿着一面锦旗,因为风吹的缘故,看不清楚内容。他们从我面前涌过,步伐踏实,向楼上走去,就听有人小声说,送给储医生啊,跟着望望。
中医科门诊在三楼最西面,门北窗南。顺序过去是中药房,针灸科,理疗科。一上三楼,潮气甚重,一路过去阴森森的,墙壁上的水泥大块剥脱,撒满了一地。因为人多,我根本无法挤到前面,只好在人群后面竖起耳朵听声。从锣鼓静灭之后的人声来往里,我隐约听到有人惊呼:“跪下来了,叩头了,叩了三个。”“啊哟!那么多红蛋啊!”“五个蛋,养的儿子。”“听说吃了三十帖汤头就能养了。”“你以为储名医的名头是虚弱佬?”
这阵欢闹足足有半个钟头,等所有的人群都散去,我来到门诊。还未进门,就闻见有奇妙的香气。大门开着,病人分几排,有站有坐,完全挡住了位置其中的医生,只是能听到非常文雅的声音在叮嘱谁,是道地的吴语乡音:“药要多泡少笃,就吃头煎,早晚分两次,晚上一顿,热水烫温了吃。饮食不忌嘴,要多睡,五帖以后来复诊。你走好啊。”
我不敢打断他的治疗过程,只是心里熬不住,急切地想知道,这个被其他医生称为疯子的人,到底是何等模样。此时,我发现了奇妙香气的来历,是他窗台上的一排绿色盆景,没有花。其他都不认识,唯一能说得出名字的是仙人掌,因为它有刺。一定是热烈的春光,催生着绿色植物茎叶的挥发,混合了屋内的文雅之气,才会有这奇妙香气的诞生。
终于可以近距离观察他的容颜举止了。
他端坐在椅子上,穿着中式的对襟上衣,亮青色的,有点发白,浅灰的直筒裤子,白棉袜黑布鞋。大约中等个子,偏瘦,看面相五十不到,眼角有细微的纹理,头发后梳,有板有形,黑白斑驳,略微髡顶,五官并无离奇之处,眉毛偏长乌黑,眼睛里能读出阿弥陀佛。阳光从窗外的天空照耀下来,照着他的背影跟侧影,背景是一排绿色的植物,他就像一株绿色的植物,不卑不亢,有种浑天然的亲和力。我心里想:有这样的疯子吗?
我把会诊单递过去,他看了看,对我说:“我上午还有病人,下午一上班就过去,好不好?”
我点头离开,转身的时候,我发现他正对面的墙上,贴着一幅毛笔字,字迹飞扬,不能识体,但三个字我能读出来:致中和。里墙有面簇新的锦旗,写的是“妙手诞麟,华佗再世”。锦旗下面的方桌上,摆着一只竹篮,盛着满满一篮子红蛋。
果然不差,下午我刚到病房,他来了。因为要进病房,我帮他拿来一件白色的工作服,他一把推开:“我不穿那东西!”
第一个会诊的就是高生平,见到储伯达亲至,他立时收起了全身的痞气,变得文静起来。
储伯达先问病史,再看病历,最后给他切脉,嘴里喃喃说道:“肝属木,肝属木……”
我不知道哪里来的急智,忽然插嘴:“肝属木,喜条达。”
储伯达忽然直身,有点意外,声音明显高亮:“你懂五行?”
喜欢文史的人,对中医都会有自然的好感:“大学里学过。”
我们前后回到医生办公室,一起洗手的时候,他忽然问我:“你晓得中医的中是什么意思吗?”
我脱口就回:“中国的医学,跟西医相对的。”
他轻轻地摇摇头,回到办公桌前,我们相对而坐,他轻声地告诉我:“于医生啊,你理解错了。知道《中庸》吗?”
我回答:“听说过。”
储伯达仰起头,抑扬顿挫地朗诵起来,把隔壁的护士都吸引过来了:“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忽然想起了他门诊墙上的字,正是“致中和”。
朗诵完毕,他解释道:“我们中医的‘中’,是‘致中和’的‘中’,‘中和’是世界万物存在的理想状态,通过各种方法达到这一理想状态叫‘致中和’。面对病人,我们中医跟西医不同的是,讲究如何让病人经过治疗,达到自身理想状态,从而能强身体,御百病,而不是仅仅着眼于眼前的疾病。持中守一而医百病,也是同样的道理。所以,中医讲究五行,讲究阴阳,讲究气血津液。简要概括的话,我们常常讲到的辨证施治,就是致中和的致。”
有小护士嬉笑着插嘴:“储医生,你不肯穿工作服,也是致中和吗?”
储伯达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带着正经,讲话的声音小了一些:“在古代,医易同源,讲究天人合一,医生的穿着,也是为了……”
护士们笑着一一离开了,谁也没在意他在说些什么。
我忽然想起了一个长久以来的问题:“储医师,我不太明白,中医的‘证’,为什么不是‘症’呢?”
储伯达笑了,笑得很开心:“于医生啊,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说明你是个爱动脑筋的人。好,我来解释你听,中医的‘证’,为什么不是西医的‘症’。你对比一下,西医的‘症’,有个病字头,表明是疾病引起的外在表现。按照西医的说法,‘症’就是一个疾病的病理生理的外在表现,它是局限的,局部的。我们中医的‘证’呢,是证据的证,证明的证,它表达的,不仅仅是疾病的病理生理,还包括病人自身的情况,譬如病人的胖瘦、嗜好、性格、行为习惯,甚至工作跟家庭情况、发病时候的天气早晚、阴晴圆缺等,都在这个‘证’中,你看‘证’,是个言旁,言正为‘证’,用我的话来讲,能对医生讲的一切,且不能是谎言,都是‘证’,都对治疗有帮助,它们,都是可以纳入阴阳五行之中的东西,于医生,你能明白了吗?”
老实说,我不是很明白,但为了那点虚弱的自尊,我还是点了点头。忽然又担心他会反问我,再摇摇头。
储伯达温和地解释说:“我举个例子吧,嗯,就说今天吧,你们为什么要请我会诊啊?”
我毕恭毕敬回答:“因为病人的小谷丙啊。”
储伯达问我:“你想过道理没?”
我摇头。
储伯达似乎在回忆,缓慢地一字一句地说道:“《金匮要略》是这样说的: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四季脾旺不受邪,即勿补之。中工不晓相传,见肝之病,不解实脾,惟治肝也。”
储伯达说完,见我眼神发愣,知道我没有明白,自己也笑了,轻轻点点头,对我说:“于医生啊,这不是短时间能通晓的,我简单地讲吧,在中医看来,肝属木,喜条达,脾属土,能生木,肝气的上升,需要脾气的推动,所以,中医治肝病,先实脾,用土话讲,叫夯实基础。反观你们的用药,眼睛仅仅盯在降谷丙的药物上,像强力宁,其实也是甘草的提炼物,只是针对肝脏的,就像书上说的‘中工’。而我的方子里,除了针对肝脏的药物,会有健脾理气的药物,这样对降低‘小谷丙’有较为理想的效果。”
因为内容太多,我更加糊涂了。静静地反思了半天,把他所有的话联系起来,随之却产生了更大的疑问,我认真地问道:“储医生,听你刚才的话,你对西医也很了解,为什么你会反对中西医结合呢?”
我话音刚落,储伯达脸色顿变,再也不理我,低头开他的药方,直到离开也没有说一句话。
他的药方很快起了作用,高生平就是生动的例子,他服用了储伯达十帖汤药,谷丙指数就正常出院了。我更加不解:为什么叫他疯子呢?
这个疑问不久就有了答案。说不久,也是一年之后的春天了。因为,在这“不久”之中,我也慢慢地成为了医院的另类。我在工作之余,喜欢看中医书,虽然不能全明白。我不精通古文,有一段时间买了一本《中庸》天天翻阅;我不会写毛笔字,就用钢笔抄了两句话,压在我自己办公桌的台板下面:不偏为中,不易为庸。不止这些,在这“不久”之中,有关储伯达的很多信息,慢慢地汇集到我的心里。他家世代行医,祖传的医术;他是一九八〇年代全市评选的十大名医之首,每月有市政府发放的津贴;他的长子在将要毕业那年,忽然失踪了;他的次子虽然学的是医,却是西医,未遵父命,让他伤心很久;他的夫人曾经是他的学生,跟他学了中医,也做了中医;他好酒,常常一边看医书,一边喝酒,还会喝着喝着哭起来;最新的奇谭是,他跟医院的医教科长张志高打架了。
那天下午,将要下班的时候,春意的天空忽然阴郁了起来,似乎是忧愁上心了。我因为“三基本”考试报名,来到医院的办公大楼,刚到一楼,就听到楼上有争吵声音,我继续往楼上去,刚到二楼,就听正对楼梯的医教科里,储伯达高声质问张志高:“我一直没点头,你哪能背着我做这种事体呢?”
张志高似乎理屈气短,声音也小了许多:“储老师,储老师,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决定。”
“那我的道理你讲了吗?你这个小人,太龌龊了。”储伯达骂声响亮。
“储老师,储老师啊,你不能骂人啊,我是为医院好,也是为你好啊。”
“放你的稻草屁!走,我们一起找院长去。”话音刚落,就看见储伯达揪着张志高的衣领出了医教科的门,要往三楼拉去。
此时,医教科隔壁的护理部忽然窜出一人,上前就拉储伯达的手,嘴里高声喊道:“储疯子,你放手,你个疯子。”
我定心一看,是护理部主任林秋芳:她怎么会拉偏架的?
我还没还过神来,我身后的楼梯“噔噔噔噔”一阵乱响,从后面冲上来一个人,上去就揪林秋芳的头发,嘴里也不干净:“你个小婊子!你放手,男人的事情你插什么横杠啊,你个不要脸的小婊子!”
我有过耳闻,终于看到真面目了。这就是储伯达的老婆阚菊花,也是本院的中医。
四个人撕打在一处,嘴里相互骂着,终于触及了皮肉,最终被拉开的时候,脸上都挂了花。事情过去一个月之后,处分出来了,阚菊花被调到了中医院,张志高跟林秋芳夫妻扣除一季度奖金,储伯达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