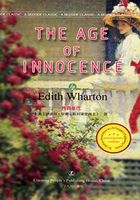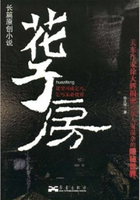到了内科我才知道,宋院长脑溢血住院,已经一周了,出血的面积较大,抢救并不显效,一直昏迷,今天中午忽然醒了,已经交代了后事,一条一条说得很明白,家人都一一答应了。最后一个要求是,他死之后要老夏给他穿衣服。这下家里人慌了,谁也不知道老夏的住处和地址。有人想到了我,说我知道,就打了我的电话。
我来到宋院长的床前,人瘦得皮包骨头了,插着一切该插的管子。我急忙趋前,俯身贴脸过去,轻轻地呼唤他的尊称,他点点头,指指身体,指指放在床头的寿衣,我对他说:“我会告诉老夏的,他一定会来的。一定!”
宋院长再次点点头,闭上眼,就再也没有任何的话语和表情留给这个世界了。只剩下呼吸和心跳。
老夏是我下午请假去请来的,到病房已经是四点钟左右了。宋院长还是那样,只剩呼吸和心跳,医生仍在继续用药,没有宣布死亡。老夏一见之下,就开始流泪了,无声无息,却极其痛苦和伤心。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会如此流泪,而且是毫不掩饰地,坐在那里,流啊流。我怕他过度伤心,会伤及身体,他说,他一定要给老院长送终的,要看着他走到另一个世界。而宋院长,再也不能看到老夏了。
我,老夏以及宋院长的家属,一起围在宋云溪的床边,已经六个小时了。大家都不说话,老夏也早已停止了哭泣,家属正在小声地商量着,大概会有多少人来凭吊,要做多少黑袖套,多少白布衣,多少红帽子等的细节,并由宋院长的长子在一一分配着任务。晚十点左右,宋云溪开始出气多进气少,点头样地呼吸了,手脚渐渐冰凉。大概是十点四十五分,宋云溪院长呼出他的最后一口气,去了一个没有纷争,没有权力地位高下之分的世界。
医生宣布,临床死亡。
哭声由小及大,连成一片,似有山呼海啸的气魄。因为宋院长的子女和亲戚实在太多,都想拥到床前来看他一眼。护士拔去所有的插管。这一刻,老夏开始工作了。他招呼子女,打来热水,照例捂嘴,合嘴,全身细细地抹一遍,穿衣,套裤,照例是上四下三,再穿袜,套鞋,全是新做的寿衣。这一回,老夏破了个例,从开始到结束,没有抽烟。我在一旁帮忙,他此刻反倒没有流泪,一直神情严峻地做着早已经习惯的一切。但不是机械的,而是带着感情在做这一切。他的每一个动作,都比平常缓慢而轻柔。
在老夏很神圣地做这一切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了几个月前,看了老夏的检查手稿后,在两难的思考和选择中,度过的那一段浑浑噩噩的时光。两个老夏,哪个才是真实的呢?现在,我看他做完了这一切,我懂了。老夏这一生,给无数的临终者穿过衣服,亲手送他们步入天国。他一定是在做这一切的过程中,领悟到了,生其实比死要艰难得多。一个人死了,不管生前如何,盖棺定论了,没有人会再不依不饶地去羞辱他,而且,绝大多数人,都可以很体面地穿上新衣,在亲人的哭声和哀怨以及挽留声中,在哀乐的细语里,在花圈的环抱中,在烈火中潇洒地走远。而活着的人呢?也许每天都要经历心灵的折磨,肉体的病痛,金钱的窘迫,自尊的挑战,还有许许多多你想也想不到的灾难。你时而开心,时而痛苦,时而开怀畅饮,时而食不果腹,谁也不能猜到,明天会有什么降临到你的头上。而你,作为一个活着的人,只有一条路,就是勇于面对。从这个意义上说,选择死要比继续生,容易得多。选择生而不是自觉地弃世,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当你的一生,风风雨雨,一切都有过经历之后,并且,你还生生地活着,你才可以骄傲地说,我没有白白活一回!老夏,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才仍然是我心目中,那一个骄傲正直、坦荡无私和见识卓越、勇于面对的男子汉。他是一个真正的人!
我为我自己以前的浅见和误解而心生不安。
宋院长的葬礼极其体面,无数的花圈,无数的被面,无数的挽联和花篮,三朝后,是无数的车辆,载着以上无数的东西,沿着县城,绕了一圈,才向火葬场慢慢地步去。无数的荣耀和赞誉,都毫不吝啬地献给了他。他走得很好。我和老夏,没有出席最后的答谢宴会,我是没被邀请,他是被邀请而没去。
过年了。
又是一个大雪年,年前,很多人忙着办年货,跌断了腿,年后,很多人忙着拜年,跌折了臂,那年春节,骨科的病人,加床加到了走廊外面。我忙得焦头烂额,第一次知道做外科医生,也会苦不堪言的。到了正月二十几,我才有时间去拜老夏的年,而且是中午我千方百计挤出来的时间。只坐了片刻,老夏又老了许多,但精神还可以,他拿出一张红请柬,是他女儿要结婚了,时间定在下月的二十八,也就是阴历的二月二十八。他说,医院就请了我一个人,要我那一天务必到场。我一口应允,表示绝不爽约,老夏才恋恋不舍地和我分了手。
县城的婚礼,程序大同小异,一般中午请两边的父母亲和亲戚,晚上是双方的朋友和单位的同事以及领导。我的请柬上,写的时间是晚六点到“兴隆大酒店”,我五点半就到了,没看到老夏,问他女儿,说是中午高兴,酒喝多了点,回去睡觉了,晚上肯定到的,要等他来才开席的,这是规矩。我看看表,确实没到时间,那就等吧。我比一般人心急,盼着他早点到来。因为在现场,除了新娘和老夏,我谁也不认识,觉得有点尴尬。
六点到了,老夏还没来,宾客们开始有点焦急了。我更急,新人站在门口也急,团团乱转。阴历的二月,天还很冷的。又等了一刻钟的时间,宾客们开始不耐烦了,交头接耳胡乱地猜测起来,猜他中午酒喝多了。我自告奋勇,和新郎的弟弟一起,坐上他的摩托车,到老夏的住处去看看。远远的仍旧是没有路灯,车速很慢,我左指右引,好容易才开到老夏的门前,一片黑暗,难道不在家?我先敲门,门从里面锁着,推不开,我怕他酒多,醒不来,用力狠命地敲门,不对,有气味!新郎的弟弟凑过来一闻,嘴里说:“啊呀,这是煤气味道么!”
我脑子里“轰”的一声,想也没想,用力一脚踹开了大门,摸索着找到灯的开关,一看地上的情景,我差点晕厥过去。
房间的正中,藤椅被拉到了墙角,炉子烧得旺旺的,水壶里的水直叫,满屋的水汽和雾气。紧靠炉子,是一只木盆,沿着里线,放着四个水瓶,老夏呢,赤身裸体,头耷在盆外,脚泡在水里,斜躺在水中,右手拖在地上,左手抬着,放在木盆的边沿上。床上,依次摆放着老夏的衣服,从里到外,全是新的,一定是为了女儿的婚礼特意做的。我忙托起他的头,用手摸他的颈动脉,没有搏动。看瞳孔,没有反射,身体已经开始冷了。我忙叫新郎的弟弟去打电话,叫救护车,一边为他做人工呼吸和心外按压。等了半个小时,救护车到了,随车的医生一看是我,问明情况,再仔细地检查了老夏,很遗憾地告诉我,死了。初步推断的死因是:煤气中毒。
老夏——一辈子为无数的死者穿衣套裤的,体面地送他们到另一个世界的——老夏,自己,却赤身裸体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事后对死因的无数猜测,对于老夏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也许是酒多了,也许是门太紧了,也许是疲劳了,也许……这许多的也许,对老夏来说,不过是鲜活的人生片段的某个链接,瞬间就猝不及防地,断了。到底是哪里断了,谁也触摸不到的,也无法修补的……
今天是我的夜班,我想起了晨会上的话,医院要重新规划了,靠南墙的太平间、木工房和配电房,都要拆了。我做完所有的事情,看看表,十点多了。我想了想,决定再去太平间看看。这间旧的太平间,在三年前就已经不用了,但医院里的人,仍旧称呼它为太平间,没人愿意靠近它。老夏的小屋,仍旧是那样孤零零地,斜接着太平间,没有一点儿生气。整个一片旧屋,也没有丝毫的亮色。我放慢脚步,来到小屋的门前,静静地停住脚,闭上眼,就在闭眼的那个瞬间,我听到了老夏在洗澡时发出的阵阵水声,而在那断续的水声中,我仿佛听到了老夏,在凄婉缠绵地哼唱着那句戏词:未开言思往事心中惆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