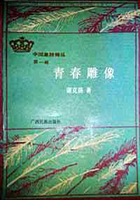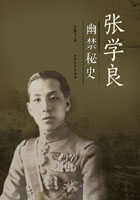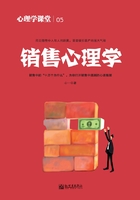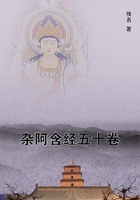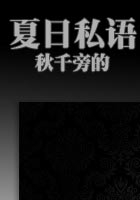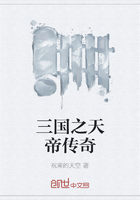《人世间》原来是这批书中的一本,那批书可是大名鼎鼎,影响了一大批人,而我是最早受到的启蒙者之一?历史有时体现到一个具体的人身上就是这么神奇,像上帝偶然安排的。那么我是怎样得到《人世间》的呢?现在完全记不清了。那么《人世间》在那个混乱年代究竟给了一个少年怎样神秘的影响?难道我的思想起点已经从读谢苗巴巴耶夫斯基就开始了?我不这样认为,我那时只有感受,潜移默化,不可能有思想,但事实上这也正是真正的文学对人的作用。潜移默化——《人世间》给了我一种人的东西,人性的东西,让我具体感知到历史宏大叙事中的个人的痛苦,使我关注到自己的内心与灵魂,并让我在冥冥中以感同身受的人性角度,超越了当时的历史叙事与意识形态,比如“在党的十一大召开的日子里”那种叙事。我不能想象如果没有《人世间》,我能否超越,能否写出关注个人痛苦的作文,甚至小说。
想想在读《人世间》的前后我都读过什么书吧:《小五义》《大八义》《三侠五义》《平山冷燕》《说唐》《隋唐演义》《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说岳全传》《封神演义》《平原枪声》《敌后武工队》《大刀记》《桥龙飙》《铁道游击队》《沸腾的群山》《金光大道》……
我不能说这些书对我没有帮助,某种意义上有很大帮助,但是它们缺少文学中最关键的东西:人,人性,复杂性;人的情感,情感的深度;心理,心理的恒定真实与瞬时的真实。而我所读到的革命与武侠演义、历史的风云际会,其中个人是微不足道的。我有着原生的血性——这是我当时只能读到的中国文学作品所给予我的,同样,我也有着能意识到的内心深邃、细微的人性痛苦,这是《人世间》给我的启发。无疑后者是文学之道,文学之途,一部《人世间》孤立其中,如此的偶然,却决定了我。
有价值的东西有时真的不需多,一点即可。说到底有价值的东西必来自心灵,来自心灵对心灵的打动。苏联文学尽管像我们一样受着强大的历史叙事与意识形态左右,但它毕竟有着强大的人文或人道主义传统,有着普希金、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丰碑。即使斯大林时期仍产生了肖洛霍夫、帕斯捷尔那克、索尔仁尼琴、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这样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和诗人,反观我们,我们产生了谁呢?《沸腾的群山》《金光大道》《智取威虎山》?我无意贬低我们自己,但我的确在上世纪80年代四顾茫然,我们不荒凉吗?
特别是80年代初,俄罗斯、欧美文学大批涌进来,我像发现新大陆那样如饥似渴地读名著,越读心里越难过,越读越觉得汗颜,感觉我们是被整个世界抛弃的孤儿。我们有多么荒凉就有多么孤独,当我读到《百年孤独》的时候,我感到我们的孤独远胜于拉丁美洲的孤独。假如我二十岁之前读过巴金、茅盾、沈从文、老舍、曹禺、张爱玲,我的孤独感是否会少一些呢?我想是这样的,但是我的整个阅读基础是在十年“文革”中度过的,我根本不可能读到祖国文学的精华,仅有一个鲁迅也成了一个政治符号。
80年代的外国文学之于我,无疑是荒凉之上的圣殿。从1979年我上大学开始,差不多长达十年时间,包括在西藏的两年,我都在读外国文学作品,小说,诗歌,传记,哲学,随笔,甚至书信。我上的是分校,走读,那年我能考上一所大学分校已实属不易,多亏了林乎加先生爱惜人才扩大招生,才有了我的大学生涯,我相信那年上分校的一万八千多名学子永远会记住林乎加,感谢林乎加。我读的那所分校是由一所中学改成的,没有图书馆,临时搭建了一排活动房当作阅览室,大量进书,订杂志,包括《世界文学》。
书都是崭新的,主要是外国文学,就是在那样一个简陋环境里(当然也常去北图),我读了难以计数的外国名著。像《九三年》《悲惨世界》《红与黑》《多雪的冬天》《大卫·科波菲尔》《约翰·克利斯朵夫》《唐璜》《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当代英雄》《爱丁堡监狱》《复活》《红字》《洪堡的礼物》《安娜·卡列尼娜》《鼠疫》《老人与海》《城堡》《审判》《局外人》《橡皮》《鱼王》《喧哗与骚动》《百年孤独》《二十条军规》。我读得慢,仔细,悉心,如《安娜·卡列尼娜》,我的日记就有这样的记载:
1981年10月12日读《安娜》,认真仔细,托氏的作品有时很沉闷,开篇总是很精彩,天才的匠心,但就整体结构来说总给人一种堆砌感,事无巨细,冗长唠叨,典型的庞大笨重。但从细部来看,托氏塑造灵魂的天才是无与伦比的,特别擅长刻画人物动态的思想意识活动,他的细致漫无边际。
1981年10月14日《安娜》上部终于读完了,心灵正是在这样的承受着细致的漫长的苦读下成熟的,我相信这样的苦读精读对于我的益处将是深远的,对我的感觉器官更是一个成熟的促进。
在西藏的两年中,重读《喧哗与骚动》,也有这样的记载:
1986年6月16日重读福克纳《喧哗与骚动》“班吉明”一章,尽管读来那样恍惚,却有一种感人至深的气氛,凯蒂的性格鲜明感人,极可爱,她是傻子班吉明生命的源泉、灯盏。虽然本章写了几个人的死,但因为有了凯蒂,这是“爱”的一章。“昆丁”一章没读完,觉得颇艰涩乏味,不好,太像福克纳本人的样子。
读文学名著使我获益匪浅,尽管90年代我没怎么读书,甚至也放弃了写作,但1998年再回到文学毫不感觉吃力,一下就上手了。我想是由于那个十年苦读,特别是在西藏两年,那种天上人间如在无人之境的阅读,已如血肉般长在我的身体内部。十年悉心苦读我想应该是可以造就一个人了,我想就算我有着十年“文革”的废墟,在这废墟之上我已建立了一座圣殿。我会继续沿着人道主义的方向研究人,发现人,表现人,正如一位哲人说的:历史对人的定义下得越宏大,我们对人的研究就应该越精微——我想这是我读外国文学感受到的一条道路。这条路实际上早在我读《人世间》就隐秘地开始了。《人世间》可能至今算不上一部名著,却是我人生道路上最早的一盏灯。
2016年5月
【北京图书馆】
1971年,北海公园关闭,直到1978年3月才重新开放。没人知道当时为什么关闭,没有任何交代,后来历史大幕拉开一角,才知道是江青、王洪文等少数人占据了北海,公园成为他们“革命”间隙休憩的地方。谁说那时没有腐败?或者腐败得不厉害?这是什么性质的腐败?个人把一个著名的公共场所即所谓的人民公园据为己有,历朝历代有吗?
但我要说的不是这件事,是北京图书馆。主要是二者离得太近,一栅之隔,大的空间上看北海—北图可以看作一体。如果坐在阅览室靠窗的位子,伸个懒腰或休息一下眼睛,即可望见北海碧波荡漾,轻舟影斜,琼岛春荫。特别是冬天的雪,银装素裹,白塔显得更加素白,换句话说北海的四季就是北图的四季,没有对北海的记忆,北图的记忆是不完整的。
北京图书馆原名京师图书馆,建筑本身即是一部书,是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空间作品,后来再也找不到如此完美的结合。从北海刚一过来,右手一扇并不宏伟的朱门,但标志性的主楼气度不凡,裙楼分布两侧,形成两个面积很大的天井花园。主楼为汉白玉雕栏、石阶,类似故宫的某个大殿,龙雕显示着东方气度,整体建筑平面造型为“工”字形,预留了未来发展空间。仿木钢筋混凝土架构,其细部做法合乎清代营造则例,内有数千种不同年代的地方文献资料,从宋代最早形成规模的方志影印本,到方志发展鼎盛时期的明清两代古籍,从最早馆藏南宋辑熙殿、明文渊阁到清内阁大库的藏书,尽显古代风流。内部功能设计灵活多变,现代气息化为无形,集借、阅、藏三位一体,打破了古代“藏书楼”封闭办馆观念。读者、书籍流动起来互为通道。配楼阅览室与半地下书库,以木旋梯上下连通,方便取书。阅览室和研究室环境幽雅舒适,光照充足,瓦当屏风又提示着历史与时间。馆内花园有个小门,可直接走进北海,一见碧波与神秘的白塔,但我从没找到过这个传说中的小门。
北海重开,北图也像重开一样,那些年谁没来过北海—北图?它们无法分开,是那个年代京城最主要的地标,是精神的最高殿堂,最美风景,留有最多的记忆,且这记忆与历史相通。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但不管怎么变,北图的地标都像是定海神针,何时走到这里,都有一种走进庙堂的感觉,天不变道亦不变,都要有一种从容,心静。无论走府右街也好,走南长街也好,走景山后街也好,走五四大街也好,四面八方的人向这里汇集,那时有多少人在向心的路上?
以至常常未开门已排起了长队。排长队进图书馆当然也不正常,正常的是这里安静,外面看不见什么人,你以为没人,但里面总有人。总有人走上台阶,或从台阶下来,穿过花园、广场……排大长队是因为历史的堵塞,十年浩劫之后,书是最让人饥渴的东西。
书荒是那些年最大的荒,真是荒。艾略特的《荒原》那时影响为什么那么大?因为不必知道诗的内容,仅仅书名这两个字就够了。
而我的情况也还有点特殊,1978年高考落第,正想去当兵,北京大办分校,三百分以上全部录取,我又被收进大学。学校原是一所中学,坐落在北京南城一个叫西砖胡同的小胡同里,稍大点的车都开不进来,离法源寺与伊斯兰教协会的大绿包都很近。每天我们像胡同里的小学生、中学生一样上下学,小小胡同混合了三级学生,也算当年的一个奇观。
我上的学校叫北京师范学院第二分院,中文系,其他还有化学系、数学系、历史系、物理系。就这五个系,有的系只有一个班。中文系人最多,有六个班。整个教学楼满满当当我们这一届学生,再没多余的空间,以至第二年无法再招生,第三年也是,到我们毕业时,这所大学依然只有我们一届学生,我们自称是独生子,毕了业学校也停办了。
学校没有操场、宿舍、礼堂、主楼、阶梯教室,没有图书馆、草坪,更没有水面、树林。没有实验室、报告厅,甚至于没有教授——靠教室内的闭路电视教学。只有一个四层楼,一个篮球场。
尽管如此,我却没有任何怨言,相反觉得非常幸运。
像我这样的人,底儿那么潮,无论什么大学能上一所也算奇迹。
走读也挺好,既然每天穿过这个城市,我不妨把整个北京都看作我的大学,就如同高尔基的大学,而北京图书馆也就理所当然成为北京这所大学的图书馆。
每每走进北京图书馆,站在汉代瓦当屏风处,以及具有空间感的连接半地下书库与阅览室的木旋梯上,我都有一种深邃的大学感。窗外的北海比之未名湖甚至东湖如何?每每在北图感到一种巨大的安慰。特别是我立志于写作,作家不需要培养,无须教师,书与图书馆就是最好的老师。唯一遗憾的是这儿不是一个人一所学校的图书馆,是所有人的图书馆,每天来看书的人太多了,平时还好,一到周日就得拿号。为了一个好的座位,比如靠窗的座位,早上五点多就得起来,排在前边的有选择座位号的特权。
回想具体的借阅过程,每一个细节都有岁月的温度。通常拿着借书证先到主楼一层选书,这里有许多带有小抽屉的柜子,抽屉里有许多卡片,每张卡片上记有书名、作者、出版社、内容简介。有字母排序,一个字母是一类,抽屉是大类,字母上是小类。很多时候并不知看什么书,而是翻类,觉得是想看的书就记下编号,上到二楼借书的地方送上编号,传送带把书慢慢从书库传出,管理员将书送达手中。拿到书绕过二楼的天井,就可以到环境幽雅的大阅览室尽情阅读。阅览室的长条桌上有绿色灯罩的台灯,天阴或光线暗时,打开台灯可以清楚地看书,即使天气好也有人开灯。
西配楼是另一个独立借阅区,这里的书刊不能借回家看,只能在阅览室看,闭馆送回。与主楼不同,这里设计简单,阅览室与借书处一体,选好书到柜台上交给管理员即可。进门处同样有许多卡片柜子,上面排列着许多卡片抽屉,抽屉上标明文学、艺术、历史、音乐类别,拉开抽屉里面依然是更细分的卡片,旁边有借阅单,选好书,填写好借阅单,交到柜台即可以在座位上等书了。这里用学生证即可借阅,通常拿学生证换座位号,学生证押在阅览室前台,走时候再用座位号换回。我更经常来这里借阅,因为这里可以借到最新的杂志。我要呼吸的是当代,杂志便是最当下的呼吸。特别正是思想解放时期,必须了解当代,呼吸当代。当代与名著,我在这里保持着交叉阅读,如果我不选择文学而是选择做学问,我会更多选择文津楼借阅,那儿不仅环境好,而且是中国古典文献宝藏。在那儿可以两耳不闻窗外事,是真正的做学问之地。我相信那里做出的学问是大师级的学问,哪怕没有师承。但我要的是原创,是从古至今的原创,包括国外的原创。我需要将曾经禁锢的一切窗子打开,那时流行着罗曼·罗兰在《贝多芬传》中的大声疾呼:“打开窗子吧!让自由的空气重新进来!呼吸一下英雄们的气息。”贝多芬是冲击那个时代最强的人之一。
我就不一一列举在这儿读到的书了,你可以想象北京图书馆是一个怎样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