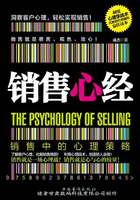“臣妾参见皇后娘娘!”才听得那珠帘一动,崇王妃陈筱敏已是起身拜倒在了地上。陈令娴亦跟随其后,唯唯下拜。
“皇婶何必如此多礼!”是赵祯的声音,傲岸而肃。他仍穿着那縠袍丝履,只将头发重梳了梳,换了顶玉叶小冠簪在髻上。绾绾则穿一件杏红乱绯的漂丝染衫,一条莞桃纱堆烟褶裙,内搭一件郁金色画罗抹胸;头上简绾着远黛髻,髻边别一朵不大不小的生丝堆纱花,花底摇下水晶两束,鬓靥缓款,柔妩不胜。二人相偕坐定,绾绾只望着,并不说话。
陈筱敏见赵祯也一同来了,本有些意外,却也沉着,声容未怠。她俯身重拜,端虔道:“令娴得蒙恩恕,是大宗正府明察秋毫,更是托赖皇后娘娘与皇上的庇护。臣妾不敢忘恩,特与令娴,拜谢皇上与娘娘!”
陈筱敏着一件杂宝罗宽袖交领披衫,一条牙白地浅嵌蟠花锦八幅裙,顶髻上戴着金笼簌叶冠,俯身时短垂的金叶明晔晔地一颤,愈显虔郑。
令娴则一直紧低着头,俯伏在姑母身后,亦步亦趋,小心翼翼。她今日着一件浅玫色的稀花纱交襟衫子,一条雪青色素纱长裙,头梳一字斜髻,髻上只有素钗数支,此外再无装饰。偶尔栖张颤仰,瞥见也是,花粉哭残,容色零薄。
“都坐下说话吧!”赵祯心地稍软,抬眼道。
“谢皇上,谢娘娘!”二人缓缓起身,却步归坐,一举一动,无不恭敬。继而两个宫人换上新茶,
“小王妃还好么?”绾绾开口问道,徐徐地,目光才落定在令娴面上。端午的那场凶险,呵,究竟与她无关啊。恨怨错恕,不由自主。
令娴受问若惊,颤颤地一恍,方惶惶抬头,应道:“罪,臣妾很好,谢皇后娘娘挂念。”
“那便好。”绾绾淡淡莞尔:“小王妃年纪还轻,凡事当自宽,万勿做绝人之想。”
“是,是……臣妾!”令娴俯一皴眉,伤由心上,恍有些顾盼的期颐,也被那历历的愁缠吞涌,不见天日。
“娘娘!”令娴忽一抬头,张仰着那悴悴如洗的憔眸,若有欲言。
“嗯?”绾绾款娜修颈,浅声疑道。
陈筱敏微微侧首顾向了令娴,那辗转的目光,柔和而深长,又有些许严肃,凝聚在那眉峰上,
令娴恍如梦醒似地,身肩冷地一吸,目光转凉。她摇了摇头,勉然道:“臣妾见娘娘,芳容若倦,想与娘娘说一声保重。”
陈筱敏这才将目光缓缓地移回,却仍沉重,心底捉摸不透的撕扯悲悯,面上却是寻常,只那眉心犹然松罥着,未知未察。
“嗯!”睹此情形,绾绾自也不再多问。
“皇婶可是为了册封的宝印宝册来的!”赵祯直言问道。
陈筱敏浅浅一笑,大方应道:“臣妾岂能这样不知廉耻,得寸进尺。”
“呵。”赵祯清冷一笑,继续问道:“那皇婶是为何?”
“臣妾只是带了令娴来向皇后娘娘道谢的!”陈筱敏仍不慌不忙,她顿了一顿,见帝后均不言语,才又道:“臣妾既入宫一趟,自然不当缺了礼数,告退后还要去拜见太后娘娘呢!”
“皇婶不用同朕绕弯子,母后近来都在静养,皇婶亦不必再费周折,有什么话,就与朕说吧!”
“臣妾确有些许微言,拟请太后娘娘示下。皇上既说娘娘在静养,臣妾自不敢再去叨烦。”陈筱敏抬眼望了望皇帝,才接着道:“近来王爷白发愈添,思想膝下空空,每生喟叹。故有意从宗室中择一近亲子侄,承祧续嗣。”
“这样的事,皇叔自己主张就是,何必来问母后,问朕的意思呢!就是皇婶的宝印宝册暂被收了,皇叔也还是朕的皇叔,宗室之间,太庙之前,可有什么不妥么?”
“皇上所言,自无不妥。王爷纵犯不赦,也还有皇上,顾惜骨肉,不忍谪斥。只这人选,却实让王爷操心,更令臣妾忧心。”陈筱敏语态虽缓款,神色却执,显是不受赵祯的揶揄。
“皇婶有什么话,请一气说完。”赵祯颜色复肃,清明不欺。
“皇上明断,臣妾亦无需遮赘。”陈筱敏微一顿首,方正容接道:“宗室近亲中,濮王与越郡王还有蜀郡王自不敢望。允谊虽年幼,稍显顽皮,也是商王妃掌上明珠,夺之不得。允谐允谧等虽系庶出,但商王舐犊情深,料也不舍。这样想来,太宗皇帝的子孙,就只剩故楚王之后,谪在禹州的允谨了。允谨也于前年谢世,惟余一子赵昳,才只八岁。”说着,陈筱敏促然起身,俯身一拜,惶惑稍露地,道:“便是这赵昳,臣妾以为,不敢做主!”
赵祯听到故楚王,原也有些吃惊。但到底事过境迁,亦不必太拘心劳思。他望了望陈筱敏,沉稳复诘:“那皇叔的意思呢?”
陈筱敏不假迟疑,恂然道:“故楚王之后,系累罪之身,王爷有什么意思,也是禁中糊涂。”
赵祯闻言思量,百辗翻覆间,取舍甘断,心潮实不安。翻一转眼,却见绾绾正栩栩凝睛地望着他,那毫无侈想的纯净,让人安心的爱恋。他唇齿惚悦,心下一时都净,才回神正色,悠悠道:“故楚王之罪,罪在前朝。允谨生于伶仃,飘蓬一世,后辈也算无辜了。果蒙恤悯,朕意不阻!”
陈筱敏一时默然,无语应接。
“童蒙之心,最是单纯。皇叔尚且自披罪责,允诚允谛更在不赦,朕有疑,崇王府又如何担负教养之重。”赵祯接着又道,语意似逼。
陈筱敏低眼徉思,一会儿才道:“臣妾不知,故而说,不敢做主!”
“皇婶。”赵祯直视眼前,穆然道:“此系善举,朕本不否。但皇叔心地反复,朕才意有存疑。若皇叔果有意收恤故楚王之后,那就请皇叔让出爵位,隐退朝堂,从此含饴弄孙,颐享天年吧!”
陈筱敏本来意念分明,悉理从容,到此却两面忡怔,进退维谷。所幸她一向眄度端庄,气质殊胜,是时亦不过俛身一福,道了声:“是!”而未至仓遽。
“那孩子也是宗室骨肉,理应被善待!”说罢,赵祯便与绾绾起身入内了。
“姑母……”令娴怯促起身,在陈筱敏身后细声唤道。
“走吧!”陈筱敏款然提袖,停盈转身,便向外去了。
自崇庆殿出来以后,芸素与另一个婢女花吟将两件薄狐氅分别披到了陈筱敏与令娴的身上。
望着天边一线幽明,摇摇欲坠,丹楼层城在其中若隐若远,迢迢连阙,都如沉睡。陈筱敏不觉抿唇一莞,不知为何。
“姑母,你很留恋这些东西么?”令娴提起那镶裹着金丝华珠的锦地氅襟,张目问道。
“我自保,也保你,有什么错么?”陈筱敏淡然应道,目光仍向着那远处,愈远愈沉。
“可是姑母,我差一点,差一点就……”令娴想起这一切的辛酸动荡,只觉荒诞,痛苦,不能卒咽。
“你的婚事,是我为你做主的,我对不起你!”陈筱敏一面走着,一面道:“我真不该听你父亲的挑唆,一味助他攀附。什么王子皇孙,天生贵胄,我自己经历过的,竟还犯这样的糊涂。崇王府中没一个有出息的,允诚,呵,他根本不配你,我一早就知道的。”
“他已经死了。”令娴抬眉,空洞道:“说什么都没用了,他死了,我也完了。”数月以来,想起这事实,令娴都还不大相信。如午夜做的梦,真假悲喜,界限模糊。多少冥心的幽恨,日子一天天的延宕,到此竟已滑跌末路,戛然崩殂了,又有谁能信呢。
“你还想他么?”陈筱静气问道。
“我想他……他活着跟死了,对我有什么区别。”令娴幽幽地应着,瞳影渐朦,盹盹如寐。
“娴儿!”陈筱敏担忧关切地一唤。
“我没事!”令娴微俯着摇了摇头,才重展眸关,望着这臧黑飘摇的宫城。
“娴儿!”陈筱敏又唤了一声,心神未定。
“姑母,如把那孩子接来,就让我来抚养照顾吧。”令娴凄凄弥瞻着眼前灯晕融融,霜飞无边,道:“我一定保护他,一定,把他教成和我一样的,不,比我要好,比我好得多的人!”
“好!”陈筱敏亦向令娴望的方向望去,心心念念,不知又望到了什么。
漏声迢递,迢迢无尽;宫灯覆影,琚佩清扬。走在这路上,一程即一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