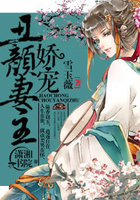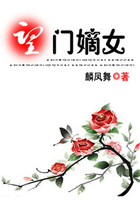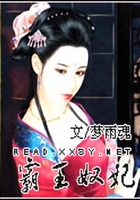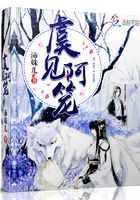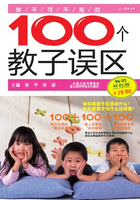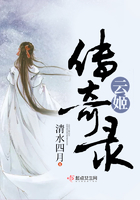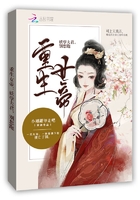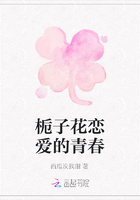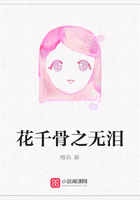又是大雪封城的一日,南谨里内却是车马拥塞,人声喧沸,叫卖茶果的摊贩们也较平日更为奔走热络。描花钿的,串珠花的,兜着满篮子红白梅枝的卖花人们也都纷纷攘攘地聚到了勾栏前。一串串鞭炮在彩帜结张的高楼上响开了,人们捂着耳朵,躲也躲不开,隆冬深寒的天气里,是更加热闹了。
这十一月初八,正是玉生蝶玉老板封场演出的日子。
奚廷好容易才寻着一处妥当地方将允谚和煜臣的马停好了,待他折回场中去寻二人时,台上大戏已开,只见乱朱成碧的一阵旗云,先有几个身手矫劲,白袍飒踏的武生穿云箭似地翻上了台来,紧接着又是一阵翮浪翻滚,翎彩纷繁,其中纤绸缓带,轻绮弄巧,翩翩地飞过了几个散花的天女,而后笙歌缓和,云蒸霞蔚,由行中脚色扮演的各路神仙才纷纷上场。天庭凸出,身材矮小的寿星身上跨着金粉漆过的松杖,手里捧着脑袋大小的手套,粉妆秾丽的脸上笑似顽童;福星则穿着与朝官相类的朱袍,与寿星身量一般,手里拿着鎏金福字,动辄挎带便颤,引人发笑;还有正旦扮演的天妃娘娘,捧花仙女,眉间眼角,悉风采秾丽。众仙在台上分分合合地唱着,贺的是一出《梨园上寿》,一时间鼙鼓喧艳,飞花乱眼,台下更是掌声雷动,红绡无数。
奚廷见惯了这些热闹戏码,哪有心思去看的,他只一心去寻允谚,故捂了耳朵梭没在了人丛中。转出数行后,他
“王爷,这玉老板才多大年纪啊,怎么就庆上寿了?”
“这原是梨园行中的规矩。”煜臣解释道:“凡有名伶谢幕,子弟后生们便在场中为前辈献这一场《梨园庆寿》,一来是对前辈的向慕尊敬,也是梨园行当代代承续,薪火相传的一个意思。”他因上次受了些寒,今日穿的更厚实了些,是一件淡青地络竹缎麋皮里的袍子,外面披着白狐里子的缬羽缎风氅,足上蹬一双浅绣金云梅杭罗绒履,头上束一根素色环纹绡抹额,嘴唇微微有些泛红,愈发显得面如冠玉。
“哦!”奚廷一口灌下一杯热茶,又问道:“那玉老板呢?玉老板多早晚才出来?”
“你急什么?总是会出来的就是了!”允谚笑喝道。他穿一件浅葱色若羽缎直身夹袍,外披一件松绿地绣连枝五色荷的狐毛氅子,腰勒素带,足登缃靴,头上束一根翡水缎抹额,也被冻得面白胜雪的。
说话间,已有兜着花篮的卖花人行到了客座间,有两鬓斑白,弓腰蹒跚的老媪,有方巾覆额,身着花边比甲的少女,甚至还有七八岁上下的垂髫顽童。他们款着花篮穿停在人丛中,或羞或进,遇客辄问,每枝折梅悉取一文。
允谚与煜臣先已觉到了些清香,待卖声接近时,二人抬头去看,只见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女,虽是肌容黄瘦,衣衫伶仃,却十分整洁。她身后还跟着一个五六岁的男童,一样的黄瘦,一双眼睛圆溜溜,兀突突地打量着四处的人,这男童穿的虽多,却都是些春秋里的夹衣,一件件叠起来的,想来也不大暖和的。这少女有些腼腆,每凡开口都要咬一咬那冻得发紫的嘴唇,十分为难似的。男童则一直抓着少女的衣服,每待少女开口,都抓得更紧了。
允谚俯低了身子,小声道:“煜兄你不知道吧,平日里能在这些地方卖东西的,都是与了银钱,和管事的人说好了的,像这对姐弟这样的穷苦人,除非是今日这样的日子,勾栏中门庭广开,否则如何进得来的。”
“王爷,你怎知道人家是姐弟,兴许这小屁孩儿是那女孩儿的丈夫呢。”奚廷虽是插话,也放低了声音。
“我就说呢,今日场中这样热闹。”煜臣温言应道。
这三人说着,那少女与男童已经走近了,煜臣温和一笑,自蓝中随拣出了一枝白梅,允谚则自袖中摸出了一粒数两重的银稞子,悄悄地握到了少女手中。
“这……这……”那少女忽然紧张了起来,双颊霎地红了,她望了望自己的花篮,又望了望眼前这几人,又颤又忙地说道:“我这儿还有好些花,二位公子不嫌弃的话……”她的口音也有些特别,像是京郊一带的村声。
“好了好了,没事的啊!”奚廷也递了一文钱过去,取过了一枝白梅,一面蔼声道:“天气太冷,你二人穿的单薄,早些回去吧。”
“是,是,谢谢二位公子,谢谢小官人。”那少女草草地一福,逃也似地走远了。
待台下红绡都掷尽,台上方仙霞云散,流绮飘逝。只留下满地的彩屑,待大幕再开时,也便不见了。
“是该玉老板登台了吧!”奚廷又忙不及待地追问道。
“嗯,该是差不多了。”煜臣从容应着,自捧过手边落了雪的温茶呷了一口。
“诶,说起来煜公子怕冷,怎么不到那楼中去坐。”奚廷见煜臣那余温尚暖的茶杯,一时没有撒手,遂问道。
“呵,这个嘛……”煜臣笑了笑,没有说话。
“这露天场中才有市井之趣呢,是吧,煜兄。”还未等煜臣说完,允谚便接话道。
“呵。”煜臣又是一笑,仍不啧声。
这时鼓角声动,动又乍歇,似起未起间,清笛已啸,笛音酿出长长的一股,混入喧杂的瓦肆中,如清酒入腑。台下一时也安静了许多,楼间场中,都齐齐地望台上看去,只见台侧景楼上一弯清清浅浅的灯晕,隐出青纱帐外,朦朦溶溶似却夜之月,月下是一茕茕单薄的人影,看得见清衣素雪,头上步摇欹颤,映晔着青纱,星星点点,侧目时睫影历历,月下神伤。
有婉怨清音自帐后传出:“黄泉别,哪知更胜生死别,想当年血流枯草,荒冢白骨无姓名。到如今,望乡台上,望人世烽烟,更隔几重,撕裂了肠肺,哭不到,再见天明。”随她声腔悱恻,一时座中都屏住了声息。过了一会儿,那女旦止了柔吟,又吟出一律,细听是:“昔日罗裳化作尘,空将业果恨前身,十年露冷枫林月,此夜处逢人面春。白杨风雨绕孤坟,谁想阳台更作云。忽启金缕箱中看,血腥还染旧罗裙。”已是凄凄哽咽,更不能言。
只有人轻声议道:“这玉老板确是行中一绝,名不虚传,不过这戏目,倒是没瞧过的!”
“外面的告牌上不是写了么?叫,叫《黄泉客》。”
“没听过啊。”
“应当是新写的本子吧,坊间传说这玉老板可是出身诗文之家的,不知什么缘故,没入了乐籍,不仅专擅音声,写的本子也较一般的书会先生词才雅正许多呢,”
“是嘛……”
说话间,帐后又添了一重灯,露出楼台迭递,永夜中梁椽萧条。台中蹑蹑怯怯地步上一头勒孝带的素衣小旦,将手提在心口,望望地又望望天,踌躇了数步,方款唱道:“十载冥泉路幽幽,虽道是人情得聚,有欢长,或更甚生时。到底惦念,这冤路血满,死生一魂,捱不尽的永夜鬼哭,长恨长离。今日得脱生天,重往人世,却不晓,不晓阿嫂何故泪落?”唱至此处,只见这小旦愁将素袖一甩,心神愈蹙。
“娘子,娘子!”又有一青衣小生,也蹑蹑怯怯地上场,挨近了小旦身旁,还未言语,先抬掸起双袖,落了一番泪。
“官人……”那小旦抬眼凝向小生,手捧在心口,也是一样的欲言又止。
“官人……”
“你我今日……”
“今日便要揆别,不知来生路上,可还有夙分,得结连理,一世的百年同心,无恨无惧。”小旦念罢,抬眼望着眼前之人,眸中泪意闪烁,说不尽的难舍难分,寸心欲裂。
“聚散无由,泉路虽好,到底不是久处之所。”小生虽如此劝解,但凝神向彼,也是十足的不舍。
见小旦仍犹豫难决,小生又加宽解道:“兄长说,天下已大定,得一太平世道而活,也算报了你我前死之屈,乱离之恨。兄长为你我殡葬骨肉,使你我魂有所依,蒙赦超生。此是兄长的一番仁心,不可辜负了。”
“说的也是,哪有不愿做人,倒要做这孤魂野鬼的。时候不早了,你我也该,也该去了。”小旦又微微地一辗目,多少的不舍,都是定局了。
“是,该去了,鬼门关前不留人,来世夙分,还交来世定。”这一生一旦偕唱着,便抟台去了。
煜臣听到此处,想到些情长缘浅的无常无奈,不禁有些黯然。故抿了一口茶水,向允谚道:“诶,谚弟,这戏才开场,就已说到了结局,过后又如何周旋承转呢?”
允谚俏皮地一笑,应道:“若你以为结局已定,那便真小瞧了这戏的格局,和写这戏的人了。”他顿了一顿,方接着道:“一人之悲,于世为小。这戏原说的是我朝大定之初,曾避祸南边的一个兰陵的书生,回乡的途中偶入鬼蜮,遇到了死于兵乱的妹妹,妹妹与一早逝书生朱生两情相悦,见兄来此,便托兄成媒。乱世中死人无数,白骨撑天,地府都来不及收,冤魂们便在泉路上结成村舍,聚落而居,有如人世。兰陵生见到的这个地方,名为沂陵村,里中尽沂蒙,兰陵两处的新鬼。兰陵生在此与为全贞节而自刭于郡下的傅九娘结成人鬼之好,蒙九娘与妹婿之托,并拾骸骨,使游魂得依。后来一夕往生,鬼蜮中竟万厦歌哭,不忍离去,也不忍不去。唉,煜兄啊,你说这生死悲欢,离合聚散,怎么就那么为难呢。”说到这里,允谚也心绪沉重了起来。
二人再望台上看,果然这兰陵生已上场披掇着行囊,漫向荒烟蔓草中去了。雾来雾去,溯回从之。
接下来停停吟吟,还聚还别。幽壤中欢生,掩袖时泪阑,急发箧时却又亲眼看得罗袜成尘,随风飘散。像这书生的际遇,一念困劫的余生。他凝着泪去望前路,哪里还有乡关,只是无尽的风埃散漫,吹他茕茕一身,生反比死更痛苦。
座中是愈发沉凝了,连添茶的小厮都放缓放轻了步伐。雪风呼呼地吹着,台楼上仍旧红缨招信,金箔曳灯。那些措手不及的遗憾与追忆,难以逆料的生离与死别,真不知唱的是戏,还是各自勘不破的人世。
看到兰陵生与傅九娘稗丛中再见,轻烟却乍别,不及递一语。允谚已是湿了眼眶,他将泪意收了收,向煜臣道:“煜兄,我有些憋闷的慌,我们去棚楼后走走吧。”
“好!”煜臣声息亦凝,一面起身,一面还向台上望去。
二人娑过人丛,向场外挪去。允谚说起这剧本原是饮秋作的,煜臣敛首一笑,好像明白了什么似的。
飞雪乱京华瑞霭,到处都是流连的欢声。两个少年相视一笑,目光中有些平和的惆怅。其实无论那些故事里的死生如何坎坷,无论古来诗篇如何浇酒成愁。至少是现在,他们还是只要一伸触到这盛世的温华,就不会灰心的。
可有的人,却已不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