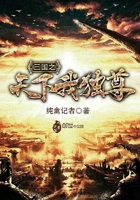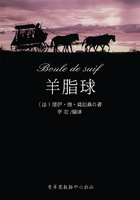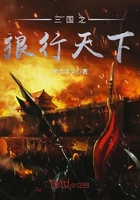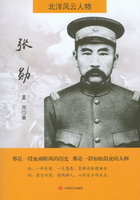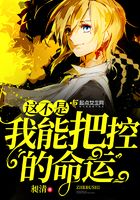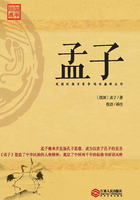1.清时期的史学特点
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老时期。在这一时期里,封建社会固有的各种社会矛盾都呈现激化的趋势,农民和地主阶级内部各种集团的冲突空前加强。生产力在继续发展,而生产关系却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新生产力的发展还不能突破封建生产关系的桎梏。
清统治者在文化学术方面,采取专制政策……对学术文化采取各种办法进行控制。第一,继续提倡八股文、尊崇孔子和程朱,以限制人民的思想。第二,查禁对于清朝不利的书籍。第三,兴文字狱。第四,寓禁书于修书。雍正、乾隆时,先后官修了《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两部大书。在编修《四库全书》的过程中,通过普遍征书而进行对书籍的销毁,通过对书籍的收录而进行删削窜改,主要目的就是寓禁于修。
这种时代特点与背景反映在史学上,一方面是因循保守气息的充斥,另一方面是反映时代抗议精神的优秀作品不断地问世。
自明代初年到清代乾嘉年代的史学,受时代的影响,呈现波浪式的变化,大致可分明代、明末清初、清代三个阶段。最后,有龚自珍的史学。
2.清初的史学和经世致用
嘉靖、万历以后,社会矛盾日益复杂和尖锐,思想领域也显得活跃起来。这在东南地区要更显著一些。明清之际,是学术思想特别活跃的年代,当时出现一些著名的学者和大师,讲求经世致用,有不少名著问世,在学术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
……从嘉靖、万历年间的“六经皆史”到明末清初的“经世致用”,这是明清时期史学的第二阶段。“六经皆史”,是要抹去作为封建统治的思想工具的灵光。“经世致用”,是要消除封建君主专制的淫威。这反映了封建社会晚期“穷则思变”的要求。但这时新生力量还很微弱,还没有可以冲破封建桎梏的能力。在封建的文化高压政策之下,到了乾嘉年代,史学的大量工作便向历史文献学和考据史学的方面转化,明清时期的史学从而进入第三个阶段……
3.清代学术和乾嘉考据
清代学术,包括的范围很广,其中乾嘉考据颇为突出。
章炳麟在其所著《检论》卷四《清儒》篇中,对清代学术有比较全面的论述。他指出,清代学术有经学,有浙东史学,有所谓“桐城义法”,有常州学派。他所谓“经学”,是乾嘉考据所开始经营的范围,后来范围扩大了。章氏说:“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多忌,故歌诗文史枯。愚民,故经世先生之志衰。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而其术近工眇踔善矣。”这是说清代学术,于理学、文史和经世之学均已衰落,才智之士为了避免迫害,大致走入说经之一途。章氏又说:“始,故明职方郎昆山顾炎武为《唐韵正》《易》《诗本音》,古韵始明,其后言声音训诂者禀焉。太原阎若璩撰《古文尚书疏证》,定东晋晚书为作伪,学者宗之。济阳张尔岐始明《仪礼》;而德清胡渭审察地望,系之《禹贡》。皆为硕儒。”他认为这些人“草创未精博,时糅杂宋明谰言”。实际上,顾炎武、阎若璩、胡渭等人的音韵、训诂、辨伪、经解,只能是乾嘉考据的先行者,他们的考据之学在清初学术上并没有多大地位。顾炎武的考据只是经世之学的手段,跟乾嘉考据有很大的区别。乾嘉考据只是继承顾炎武学术之技术性的一面,而舍弃了他的精髓。
关于乾嘉考据,章炳麟认为:“一自吴,一自皖南。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江永、戴震,综形名,任裁断。此其所异也。”
所谓吴学,章炳麟说:“先栋时有何焯、陈景云、沈德潜,皆尚洽通,杂治经史文辞。至栋,承其父士奇学,揖志经术,撰《九经古义》《周易述》《明堂大道录》《古文尚书考》《左传补注》,始精眇,不惑于謏闻,然亦泛滥百家,尝注《后汉书》及王士稹诗,其余笔语尤众。栋弟子有江声、余萧客。声为《尚书集注音疏》,萧客为《古经解钩沉》,大共笃于尊信,缀次古义,鲜下已见。而王鸣盛、钱大昕亦被其风,稍益发舒。教于扬州,则汪中、刘台拱、李悖、贾田祖以次兴起。萧客子弟甘泉江藩,复缵续《周易述》。皆陈义《尔雅》,渊乎古训是则者也。”
所谓皖学,章炳麟说:“震生休宁,受学婺源江永,治小学、礼经、算术、舆地,皆深通。其乡里同学有金榜、程瑶田,后有凌廷堪、三胡。三胡者,匡衷、承珙、培翠也。皆善治《礼》。而瑶田并通水地、声律、工艺、谷食之学。震又教于京师,任大椿、卢文弨、孔广森皆从问业。弟子最知名者,金坛段玉裁、高邮王念孙。玉裁为《六书音韵表》以解《说文》,《说文》明。念孙疏《广雅》,以经传、诸子转相证明,诸古书文义诘诎者皆理解。授子引之,为《经传释词》,明三古辞气,汉儒所不能理绎。其小学训诂,自魏以来,未尝有也。近世德清俞樾,瑞安孙诒让,皆承念孙之学。樾为《古书疑义举例》,辨古人称名抵牾者,各从条列。使人无从疑眩,尤微至。世多以段、王、俞、孙为经儒,卒最精者乃在小学,往往得名家支流,非汉世《凡将》《急就》之侪也。凡戴学数家,分析条理,皆参密严琛,上溯古义,而断以己之律令,与苏州诸学殊矣。”
这些话说出了乾嘉考据之概貌,而考据的范围包括了音韵、训诂、算术、舆地、声律、工艺、谷食之学,于经传之外,旁及子史。这些学者确实下了功夫,在古籍整理上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使一向难以通解的书得以通解,一向真伪难辨的书得以正确的理解,沉没已久的古音古义得以复现。但这些成绩仅限于很小的天地内,对于明清之际以“经世致用”为目标的史学来说,是无从比拟的。作为皖派领袖的戴震,本来既是考据学家,又是哲学家。但他在哲学方面的学术表现不只为其考据学上的成就所掩盖,而且为其后学者所讳言。风习的移人,于此更可值得注意。
关于浙东史学,章炳麟说:“自明末有浙东之学。万斯大、斯同兄弟,皆鄞人,师事余姚黄宗羲,称说《礼经》,杂陈汉、宋,而斯同独尊史法。其后余姚邵晋涵、鄞全祖望继之,尤善言明末遗事。会稽章学诚为《文史》《校雠》诸通义,以复歆、固之学,其卓约近《史通》。而说《礼》者羁縻不绝。定海黄式三传浙东学,始与皖南交通。其子以周作《礼书通故》,三代制度大定。唯浙江上下诸学说,亦至是完集云。”万斯同、全祖望对明史的工作,其兴趣在于保存明代文献,他们还有清初学者那样的民族思想。他们的工作是跟考据家的古籍考订不同的。章学诚是乾嘉年代的史学大家,他的代表作《文史通义》及方志学,很值得重视不究。
历史文献学和乾嘉考据史学,在清代学术上占据重要的地位。对此,下文做专门介绍。
对于乾嘉年代的撰述,也还值得一提的。秦蕙田的《五礼通考》,是典章方面的通史。毕沅的《续资治通鉴》,是紧接《资治通鉴》的编年体宋元史,两部为史书中有分量的作品。
最后,还要提到龚自珍的史学。龚自珍是思想家,也是历史家。他提出学说,治西北舆地,提倡经世之学,愤恨封建的黑暗,憧憬未来社会的曙光。由于当时社会和文化旧的还很深厚,尚无光明前景,故他思想上新与旧、传统与异端的矛盾交织,显示出新的不免稚弱,而旧的尚很沉重。
总之,明清史学的纷繁现象,是社会变革的矛盾运动在史学领域里的反映,有的反映得明显,有的反映得曲折,有的为封建桎梏所紧紧掌握,有的是要挣脱封建桎梏而又苦于力量的不足。至于龚自珍的史学,则透露出一定的近代启蒙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