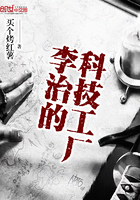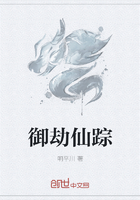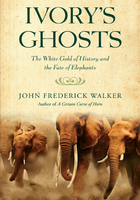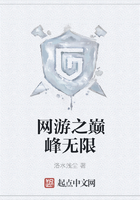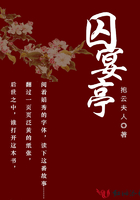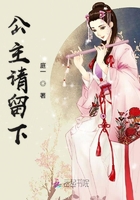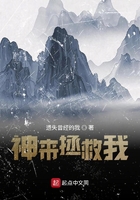1.时代的特点与史学发展趋势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时期,也是中国史学成长起来以后走向发展的时期。这700年左右历史的时代特点,在许多方面影响着史学的发展。首先是政治上的变动,出现了或几个封建皇朝并存或南北皇朝对峙的局面,而终于促成了隋唐皇朝的统一和兴盛。在这个过程中,门阀地主形成和发展起来,代替了前一个时期的世家地主,成为在政治上占据主要统治地位的阶层。这种形势推动了皇朝史撰述的发展,出现了“一代之史,至数十家”的盛况。这种形势也推动了姓氏之学的发展,谱学之书的撰述成为这个时期史学活动的时尚:“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这两条,是门阀地主政治在史学上的突出反映。
这个时期的另一个重要的时代特点,是发生了民族间的长期斗争,发生了民族的大规模流动和人口的大规模迁移。民族间的长期斗争和民族的大规模流动,使中国北部一度出现了皇朝林立的局面,而不论在北方还是南方,民族杂居的地区都扩大了,民族间的融合都加深了。这个时代特点反映在史学上,一方面,是推动了各民族政权对“国史”的撰述。《隋书·经籍志二》“霸史”篇记:自西晋永嘉之后,“九州君长,据有中原者甚众”,“其君臣忠义之节,经国字民之务,盖亦勤矣。而当时臣子,亦各记录。”隋唐时期,前人所撰北魏史被承认为“正史”,并在前人所撰基础上新撰《北齐书》和《周书》,也都列入“正史”,扩大了民族史撰述的内容。另一方面,是随着大批劳动人手的南迁和中原先进生产技术的传播,长江以南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文化风习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从而为历史撰述提供了丰富的新内容。《晋书·食货志》记有关江南水利兴修事;《宋书·州郡志》备载北方人口南迁和侨立州郡的情况;《隋书·地理志》极言扬州之盛,称丹阳“埒于二京,人杂五方”,京口“东通吴、会,南接江、湖,西连都邑,亦一都会也”,而宣城、毗陵、吴郡、会稽、余杭、东阳诸郡则“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其人君子尚礼,庸庶敦厖,故风俗澄清,而道教隆洽,亦其风气所尚也”。同书记荆州说:“其风俗物产,颇同扬州”,“南郡、夷陵、竟陵、沔阳、沅陵、清江、襄阳、舂陵、汉东、安陆、永安、义阳、九江、江夏诸郡,多杂蛮左,其与夏人杂居者,则与诸华不别。”“自晋氏南迁之后,南郡、襄阳,皆为重镇,四方凑会,故益多衣冠之绪,稍尚礼义经籍焉。”《通典·食货十》记江南漕运对于关中的重要。同书《州郡十二》记扬州风俗说:“永嘉之后,帝室东迁,衣冠避难,多所萃止,艺文儒术,斯之为盛。今虽闾阎贱品,处力役之雋,吟咏不辍,盖因颜、谢、徐、庾之飚扇焉。”《州郡十三》记荆楚风俗说:“南朝鼎立,皆为重镇。然兵强财富,地逼势危,称兵跋扈,无代不有。”《元和郡县图志》的江南、剑南、岭南诸篇,记南方的州域疆理、丘壤山川、攻守利害,都详于前人的撰述。总的来看,这时期的许多历史著作,都突出地加重了对南方社会发展进程记载的分量。历史撰述反映在地域上和内容上更加恢宏、更加丰富了。
这个时期还有一个时代特点,是思想领域中的“天下大同”、“天下一家”观念的形成,它是长时期的民族斗争和大规模的民族融合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这种观念,在当时现实的历史活动和对以往历史的认识与撰述中,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看到唐初多民族相聚的局面,唐高祖兴奋地说:“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唐太宗晚年总结历史经验,把“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看作一条重要的成功决策。这种认识,在唐代的许多历史撰述中有突出的反映。比起秦汉时期的“大一统”思想,它包含了更多的对于多民族国家之历史的自觉意识。
这个时期,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有了更大的发展,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达到了极盛的程度,这推动了关于中外交通和域外情况的撰述。贾耽的《皇华四达记》和杜环的《经行记》因原书早佚,故其遗文零简尤为人们所推重。佛教僧人在这方面的撰述颇为丰富,《法显传》《大唐西域记》《海内寄归传》《往五天竺国传》《高僧传》《续高僧传》等都是知名之作。
2.史书数量的剧增和种类的丰富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史书在数量上和种类上有很大的发展。这个发展,可以从《隋书·经籍志》同《汉书·艺文志》分别著录的史书的比较中,从《新唐书·艺文志》序提供的数字同《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史书数量的比较中得其大体:
《汉书·艺文志》撰成于1世纪末,它以史书附于“《春秋》类”,著录西汉人的历史撰述6种343篇。《隋书·经籍志》成书于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上距班固去世之年(92年)凡564年,其中前120余年是东汉中后期,后60余年是隋与唐初,中间约370年是魏晋南北朝。《隋志》史部大序说:“班固以《史记》附《春秋》,今开其事类,凡十三种,别为史部。”它称著录史书817部,13264卷;通计亡书,合874部,16558卷。它们约占《隋志》所著录四部书(道、佛二经不计)种数的1/5弱,卷数的1/3强。这些史书除极少数是东汉及隋朝人所撰,绝大部分产生于魏晋南北朝时期。
《新唐书·艺文志》序称:宋代以前,“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其著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者,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如以唐代学者所著书平均分配于四部,史部书应得7100多卷。这是唐朝开国以后大约100年间的成就。把这个数字的每年平均数,同魏晋南北朝370年间史书著述的每年平均数相比,要多出一倍左右。这是盛唐时期的情况,中晚唐时期可能会有些变化,但也不会相去太远。这说明,隋唐时期史书在数量上的发展又超过了魏晋南北朝时期。
这个时期的史书的品种、类别也增加了。南朝梁武帝时阮孝绪撰《七录》,有经典录、记传录、子兵录、文集录、技术录、佛录、道录。阮孝绪考虑到“史家记传,倍于经典”,特“分出众史”,立为记传录。它分“众史”为12类:国史、注历、旧事、职官、仪典、法制、伪史、杂传、鬼神、土地、谱状、簿录。史书不仅成为一个独立的部门,而且必须按其所记内容进行仔细分类,这是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史书在数量上和种类上的发展,跟史家人才辈出、私人撰史蔚然成风有直接的关系。刘知幾《史通·史官建置》称魏晋时的华峤、陈寿、陆机、束皙、王隐、虞预、干宝、孙盛,南朝时的徐爰、苏宝生、沈约、裴子野等,都是“史官之尤美,著作之妙选”。他论北朝史官,于北魏提到崔浩、高闾,于北齐、北周则说“如魏收之擅名河朔,柳虬之独步关右”,“亦各一时也”。私家撰史,魏之鱼豢,西晋之王荃,南朝宋之范晔,齐之臧荣绪,梁之吴均以及北魏之崔鸿,皆为名家。官史、私史是相对而存在的,所谓“尸素之俦,盱衡延阁之上;立言之士,挥翰蓬茨之下”,正是私家撰史活跃的原因之一。
3.地方史、民族史和关于域外情况的记述
地方史和民族史撰述,以及关于中外交通和域外情况的记述;还有家史、谱牒和别传,通史和笔记的撰述,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史学发展趋势中的几个重要方面。
中国史学上关于地方史志的撰述起源很早,至迟在两汉时已有了很多撰述。班固撰《汉书·地理志》时,就曾经使用过当时地方志的材料。魏晋南北朝时,地方史志的撰述有了很大的发展。刘知幾《史通·杂述》论郡书况:“汝、颍奇士,江、汉英灵,人物所生,载光郡国。故乡人学者,编而记之。”又论地理书说:“九州土宇,万国山川,物产殊宜,风化异俗,如各志其本国,足以明此一方。”前者以人物为主,侧重记社会;后者以地理为主,侧重记自然、物产。它们的共同点是记一方之史。《隋书·经籍志》杂传类著录,自《蜀文翁学堂像题记》以上,大多属于刘知幾说的郡书;地理类著录诸书,比刘知幾说的地理书要广泛得多。
今存《华阳国志》是这个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地方史著述。《隋书·经籍志》把它列入“霸史”类,《史通·杂述》把它归于地理书。其实,它兼记一方的历史、地理、人物,涉及民族、风俗、物产,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地方史。“华阳”之名取自《禹贡》说的“华阳黑水惟梁州”;《华阳国志》因所记为《禹贡》九州之一梁州地区的历史,故采古义而名之。著者常璩,字道将,生卒年不详。他出生于晋蜀郡江原(今四川崇州市),成汉李势时官散骑常侍,掌著作;入晋,为桓温参军。据今人考证,常璩撰成《华阳国志》,当在东晋穆帝永和四年(348年)至永和十年(354年)之间。《隋书·经籍志》“霸史”类还著录有他的《汉之书》10卷,当撰于成汉时期,入晋秘阁后改称《蜀李书》。
《华阳国志》12卷:卷一至卷四,是《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记梁、益、宁三州的历史概况,以地理建置、自然状况为中心,详述各州郡的山川、交通、风土、物产、民俗、族姓、吏治、文化以及同秦汉、三国、两晋历代皇朝的密切关系。每卷之下都有“总叙”,然后分叙各郡,总共为33郡。卷五至卷九,分别是《公孙述刘二牧志》,记公孙述、刘焉、刘璋事;《刘先主志》《刘后主志》,记刘备、刘禅事;《大同志》,记三州在西晋时期的史事,起于魏之破蜀,迄于晋愍帝建兴元年(313年)三州大部为李雄所据;《李特雄期寿势志》,记“李氏自起事至亡”,六世42年史事,迄于晋穆帝永和三年(347年)。这几卷,是关于三州自东汉末年至东晋初年的编年史;用汉、蜀汉、两晋纪年而黜李氏纪年,仅记其建元、改元事。卷十(上、中、下)至卷十一,是《先贤士女总赞》(上、中、下)和《后贤志》,前者记蜀郡、巴郡、广汉、犍为、汉中、梓潼诸士女300余人,皆晋以前人物,后者记两晋时期三州人物20人。卷十二是《序志》并士女目录。《目录》所收凡401人,其中有大约1/3不见于卷十和卷十一所记;《序志》略仿《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汉书·叙传》,阐述了撰述旨趣、所据文献和各卷目录提要,但未叙述著者本人家世,这可能跟他先事李氏、后为晋臣的经历有关。
《华阳国志》在编撰上有自成体系的格局,它把三州地区的历史面貌、政治变迁、不同时期的人物传记由远而近、由广而微地编纂成一书,集中记述了东晋初年以前梁、益、宁三州(包括今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以及甘肃、陕西、湖北三省部分地区)的历史,堪为这个时期地方史撰述中的杰作。常璩撰《华阳国志》的旨趣,既有史学上的考虑,也有政治上的考虑。他在《序志》中开宗明义说:“巴、蜀厥初开国,载在书籍,或因文纬,或见史记,久远隐没,实多疏略。”他称道陈寿撰的《益部耆旧传》,但认为它“三州土地,不复悉载”。又说《汉书·地理志》“颇言山水”,但“历代转久,郡县分建,地名改易,于以居然辨物知方,犹未详备”。又说“李氏据蜀,兵连战结,三州倾坠,生民歼尽”;“桑梓之域,旷为长野”,“惧益遐弃,城陴靡闻”,担心家乡的历史遭到湮没的命运。他说自己是“方资腐帛于颠墙之下,求余光于灰尘之中,劘灭者多。故虽有所阙,犹愈于遗忘焉”。这些,都是从史学上着眼的。从政治上考虑,他是要以本书证明:“夫恃险凭危,不阶历数,而能传国垂世,所未有也。故公孙、刘氏以败于前。而诸李踵之覆亡于后。天人之际,存亡之术,可以为永鉴也。”因此,他撰本书的目的是“所以防狂狡,杜奸萌,以崇《春秋》贬绝之道也;而显贤能,著治乱,亦以为奖劝也”。总之,浓郁的桑梓情感和明确的政治借鉴交织成他的撰述旨趣。
常璩撰《华阳国志》有三个方面的资料来源:一是皇朝史,如《汉书》《东观汉记》《汉纪》《三国志》;二是有关巴、蜀、南中的地方史志,如谯周《三巴记》、陈寿《益部耆旧传》、魏宏《南中八郡志》等;三是作者本人考察搜集的资料,其中当包括他撰写《汉之书》(《蜀李书》)时所积累的资料。此外,他也参考了《史记》和先秦文献。《华阳国志》在编撰体例上受《史记》《汉书》影响最大。《华阳国志》各卷后论,称为“撰曰”,雕琢字句而内容空泛,反映出常璩在历史思想上的贫乏。
刘知幾称赞《华阳国志》“详审”而能“传诸不朽,见美来裔”,指出了《华阳国志》在历史编纂上的成就。隋唐以下,史家修史,多有参据,也足以证明它在史学上的价值。
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的地方史很多,但存者寥寥,且又真伪难辨,残缺不全,唯《华阳国志》历1600余年独放异彩,使今人阅后可以想见中国古代西南地区文明发展的进程。
这一时期的史家还写出了许多当代民族史著作,但它们多是以皇朝史或“国史”的形式出现的。崔鸿的《十六国春秋》和魏收的《魏书》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可惜前者已散亡,只有节本和辑佚本流传,已不可窥其全貌了。《魏书》在民族史记述上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它还记述了拓跋部以外的鲜卑族的历史,记述了鲜卑族以外的其他各族的历史,涉及东北、西北、西域、北方许多民族,显示出在民族史记述上的开阔的视野。它在反映这个时期北部中国诸民族的重新组合和融合方面,是具有总结性的著作。
4.家史、谱牒和别传
家史、谱牒和各种名目的别传的大量涌现,都是这个时期社会历史的特点在史学上的突出反映,都是门阀的政治要求和意识形态在史学上的表现形式。
刘知幾《史通·杂述》篇说:“高门华胄,奕世载德,才子承家,思显父母。由是纪其先烈,贻厥后来,若扬雄《家谍》、殷敬《世传》《孙氏谱记》《陆宗系历》。此之谓家史也。”这里,刘知幾道出了家史的性质,它主要出自“高门华胄”,它的作用是“思显父母”、“贻厥后来”。但他举出的扬、殷、孙、陆四例,是把家史同谱牒合而论之的。《隋书·经籍志》以家史入“杂传”类(因家史多以“家传”为名),而以“谱系”自为一类。
《隋书·经籍志》杂传类自《李氏家传》以下,至《何氏家传》止,共著录家史29种,多为两晋南北朝人所撰,如《王朗王肃家传》《太原王氏家传》、江祚《江氏家传》、裴松之《裴氏家传》、曹毗《曹氏家传》、范汪《范氏家传》、纪友《纪氏家传》、明粲《明氏世录》、王褒《王氏江左世家传》,等等。南朝梁人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引用家传8种,其中《荀氏家传》《袁氏家传》《李氏家传》《谢车骑家传》《顾恺之家传》等5种《隋书》未著录。这34种家史,基本上都已不存,其中少数几种在《世说新语注》中也只存片言只语。但是,《宋书》和《魏书》的列传,往往以子孙附于父祖而传,一传多至三四十以至五六十人,从中不难窥见这种家传的形式。
家史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家谱,它是谱牒的基本构成因素。但谱牒之书往往并不限于一门一姓,有一方之谱,也有全国性或一个皇朝统治范围内的总谱。这是谱牒同家史的一个区别。它们的另一个区别,是家史都撰自私门,而有影响的一方之谱和全国总谱多出于官修。《隋书·经籍志》谱系类著录的谱牒之书,有帝谱、百家谱、州谱、家谱共34种,是属于这个时期所具有的特定意义的谱牒之书,其实际上的数量自然比这要大得多。仅《世说新语注》引用谱书46种,就有43种不见于《隋志》著录,可见佚亡的或失于著录的数量之大,从而可以推见魏晋南北朝谱牒撰述之盛。
谱牒撰述之盛导致了谱学的产生和发展。东晋南朝谱学有两大支脉,一是贾氏谱学,一是王氏谱学,而后者源于前者。贾氏谱学的奠基者是东晋贾弼之。萧子显《南齐书·文学·贾渊传》记:“先是谱学未有名家,渊祖弼之广集百氏谱记,专心治业。”晋孝武帝太元年间(376—396年),贾弼之在朝廷支持下,“撰定缮写”成书,并经其子匪之、孙渊“三世传学”。此书包括“十八州士族谱,合百帙七百余卷,该究精悉,当世莫比”。这就是《姓系簿状》一书,是为东晋南朝谱学之渊薮。刘宋时,王弘、刘湛“并好其书”。弘为太保,“日对千客,不犯一人之讳”;湛为选曹,始撰《百家谱》“以助铨序”。萧齐时,王俭重新抄次《百家谱》,而贾渊与之“参怀撰定”;贾渊亦自撰《氏族要状》15篇及《人名书》。其后,贾渊之子执撰《姓氏英贤》100篇和《百家谱》;贾执之孙冠,承其家学,亦有撰述。这都是王氏之学兴起以后的事了。王氏谱学兴于梁武帝时。尚书令沈约指出:东晋咸和(326—334年)至刘宋初年,晋籍精详,“位宦高卑,皆可依案”;后来由于晋籍遭到篡改,便“昨日卑细,今日便成士流”。他认为,“宋、齐二代,士庶不分,杂役减阙,职由于此”。梁武帝乃以王僧孺知撰谱事,改定《百家谱》。王僧孺乃“通范阳张等九族以代雁门解等九姓。其东南诸族别为一部,不在百家之数”,撰成《百家谱》30卷。他还集《十八州谱》710卷,撰《百家谱集抄》15卷、《东南谱集抄》10卷。
谱牒撰述之盛和谱学的兴起,有深刻的社会原因:“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权归右姓已。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为之,以定门胄,品藻人物。晋、宋因之,始尚姓已。然其别贵贱,分士庶,不可易也。于时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故官有世胃,谱有世官,贾氏、王氏谱学出焉。”这表明,凡“品藻人物”、“有司选举”、划分士庶,都以谱牒为据;而谱牒又须“考其真伪”,故有谱学之兴。此外,门阀士族之间的联姻,也往往要互相考察谱牒,以保证门当户对。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这种社会现象一直继续到唐代,也成为史学发展中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5.通史撰述
在《史记》以后的数百年间,通史撰述甚为寥落,而断代为史的皇朝史撰述则风靡一时。南北朝时,梁武帝曾命史学家吴均等撰《通史》600卷,北魏元晖也曾召集史学家崔鸿等撰《科录》270卷。这两部书都是通史,但都没有流传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