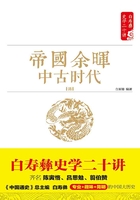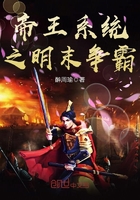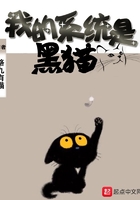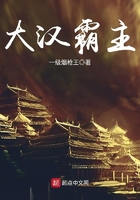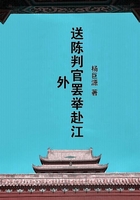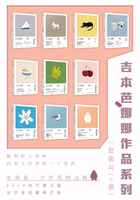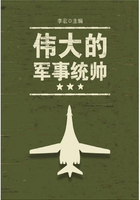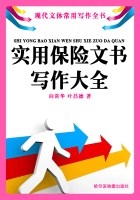1.《后汉书》范晔所著
范晔,字蔚宗,刘宋时顺阳人,公元398年生,是晋豫章太守范宁的孙子,宋侍中范泰的庶子。在世族社会中,嫡庶之别是家庭内部不可逾越的大分,同时,嫡庶之别又总是外家社会身份(士庶贵贱)的延长,因而也影响子女的社会身份。范晔生在厕所里,并且因生产时为砖伤额,就以砖为小字,这就表明这个庶子刚出世时在这一名门中所面临的屈辱。他少年时期已显露了才华,却反而惹得哥哥讨厌,说“此儿进利,终破门户”。后来范晔为后汉王符作传,始称“少好学,有志操,与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友善”,接着就说“安定俗鄙庶孽,而符无外家,为乡人所贱”;篇末终结为“书生道义之为贵”。作者于此不无身世之感。
范晔因出继从伯弘之,得袭封武兴县五等侯。他初为彭城王义康冠军将军府参军,累迁至尚书吏部郎。432年因触怒义康,迁宣城太守,在任所著《后汉书》。后来累官至左卫将军、太子詹事。以才能为宋文帝所重,但却受到同僚的嫉忌和排挤。史记孔熙先说范晔,所谓“廉直劲正不得久容”,所谓“人间雅誉过于两臣”,所谓“谗夫侧目,为日久矣,比肩竞逐庸可遂乎”,这可说明他遇到了何等的排挤。他不顾这些排挤,仍作《和香方序》,以“麝本多忌,过分必害”比庾炳之,以“零藿虚燥”比何尚之,以“詹唐黏湿”比沈演之,以“甲煎浅俗”比徐湛之,而以“沈实易和,盈斤无伤”自比。445年终于被徐湛之这般人借着孔熙先事件牵连进去,以谋反的罪名被杀害了。
幼年面临的屈辱和宦海生活中的倾轧,使范晔的异端思想有了产生的根源。后汉史事的研究,又推动了这种思想的滋长。范晔自称:“本未关史书,政恒觉其不可解耳。既造《后汉》,转得统绪。”他是在迁宣城太守后,才认真开始这一工作的。实际的政治经验跟后汉史事相证,许多“不可解”的事情就“转得统绪”了。《宋书》本传说他“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南史》本传因袭了《宋书》这句话,又加上一句说:“至于屈伸荣辱之际未尝不致意焉”。沈约、李延寿虽不能充分说出他著书的意义,但也窥测出来了一些消息。
范晔在狱中与诸甥侄书,曾从容自序治学态度、对文章的见解和对《后汉书》的期许。他说:
“吾狂衅覆灭,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然平生行己任怀,犹应可寻。至于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
吾少懒学问,晚成人,年三十许,政治有向耳。自尔以来,转为心化,推老将至者,亦当未已也。往往有微解,言乃不能自尽。为性不寻注书。心气恶,小苦思便愦闷。口机又不调利,以此无谈功。至于所通解处,皆自得之于胸怀耳。文章转进,但才少思难,所以每于操笔,其所成篇殆无全称者。”
这里首言“覆灭”由于“狂衅”,但不应以此埋没其“行己任怀”的“自得”之学。接着就说他不治章句注解之学,没有清谈的条件,而注重自己治学的方“向”,追求“自得之于胸怀”的“通解”,并且老是觉得不满足,感到“才少思难”。所谓“年三十许”,正跟他在宣城开始写书的时期相近,他左迁宣城太守的时期,年35岁。
《后汉书》记王莽末年到汉献帝逊位200多年间的史事,纪10、列传80、共90卷。志10,未及写成。纪、传例,久已失传。梁刘昭取司马彪《续汉书》中的八志以补范书,附纪、传以行。宋人刻书,以八志置于纪、传之间。
2.《后汉书》对史事的“整理”
范晔《后汉书》采华峤书序论中语,可考者约十处。他所称举的“前史”或“本书”,据说是《东观汉记》。刘知幾说他“广集学徒,穷览旧籍,删繁补略,作《后汉书》”。但他于类似因袭之中,却多有创见。如华峤书中,在帝纪之后有皇后纪,这主要是从帝后间的夫妇关系去考虑的。范晔也在帝纪之后有皇后纪,主要是从政治史上的作用来考虑的,是跟华峤不同的。
范书80传,于按照时代先后的编次之中,发展了“言行趣舍,各以类书”的方法。列传1至3,是两汉之际起义和割据的领袖人物。4至12,是光武时的宗室王侯和28将。13至42的传首人物,都是明帝、章帝、和帝时人,而分别以行止相近的人物或子孙合传。43至53的传首人物是安帝、顺帝时人,也多分别有合传的人物或子孙。54至65,都是桓帝、灵帝、献帝时人物。66至74,是循吏、酷吏、宦者、儒林、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等九杂传。最后六篇是边族的列传。
皇后立纪和列传以类相从、因人见事的方法,是《后汉书》“整理”史事的一种重要的方法。范书列传中仍不免有那种品题人物的兴趣,而因人见事的方法有时还不能明确地表达作者的意图所在。但范晔提出历史问题的兴趣,远远超过一般的品题人物的兴趣;他以类从的意义显然是远远超过“观其名迹,想见其人”的要求的。合传中虽有主题晦昧,并且因时代顺序与类从撰集的错综而使人感到凌乱的地方,这说明范晔意图发展的历史编纂法还很不够成熟,似乎他还没有觉察到纪传体对于反映历史问题的局限性。从当时史书撰集的情况来看,范晔的这些缺点并掩盖不了他在编纂法上取得的成就。
《后汉书》“整理”史事的另一个方法,是有意识地通过史事来反映自己的政治观点。这本来应该说,每一个历史家,或有意或无意,都做到了这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后汉书》反映了范晔的进步观点,表现了他的进步性。《王充、王符、仲长统传》对《潜夫论》五篇和《昌言》三篇有所删取,因它们所“究”“当世失得”,寓“指讦时短,讨谪物情”的讽喻,以期“有益”于政,这一篇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
范晔重视节义。他评论班固说:“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关,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这是把节义当作衡量历史人物的重要标准。他以此来分别司马迁史学和班固父子史学的高下,并通过史事的整理来表示他的看法。
范晔作为世族地主阶级家庭出身的历史学者,还是希望封建统治秩序稳定的。但他的《后汉书》并不在于要求人们如何服从封建统治,而是揭露了统治者的丑恶面目,并称道了那些“激素行以耻威权,立廉尚以振贵势”的人物。这样的态度就是他的异端性格,他的进步性的重要表现,这是符合当时地主阶级中日益明显地分化出来的庶族地主的政治希望和政治利益的。
范晔对于史事“整理”的成就,发展了历史编纂的方法,表现了进涉的政治态度,同时也是对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这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3.《后汉书》中的论赞
《后汉书》以明文评论史事,采取论赞的形式。它在《后汉书》中的地位,远超过《汉书》中的赞和《三国志》中的评,有时也超过了《史记》中的“太史公曰”。论一般是指纪传后面的论,差不多每篇都有一首或一首以上。论中又有序论,也称作序,在《皇后纪》和杂传的前面。论,多是评论历史问题和历史人物,有时也采取讽喻或感慨的形式。赞在每篇纪传后面都有一首,一律用四字一句的韵语写成,或概括史实。或另发新意,多可补论的不足。
《后汉书》中的论,于继承《史记》《汉书》的传统外,也受到魏晋以来某种史论的影响。正像秦汉之际的一些人关心古今之变的原因一样,魏晋以来的长期动荡曾推动了一部分历史学者关心较长时期内的历史,因而在梁武帝《通史》以外,还出现了较多的通史性的著述,如吴韦昭撰《洞记》4卷,记庖牺以来至汉魏间事;晋皇甫谧撰《帝王世纪》10卷,记三皇以至汉魏间事。总括一代以至数代兴亡大事的史论,这时也引起一些历史学者的注意了。著名的,如魏曹同著《六代论》,论夏、商、周、秦、汉、魏的兴亡;晋陆机著《辨亡论》,干宝著《晋纪·总论》,论孙吴、东晋的兴亡;习凿齿临终上疏,论晋宜越魏继汉。《后汉书》的论,就是在这样的时代影响下,发挥了作者的历史见解,其显著的特点就在善于从历史形势的发展上论述古今的变异。
《后汉书》的中兴二十八将论、《党锢列传·序》和《宦者列传·序》是著名的史论,而又各有独到的地方。如与有关的论赞合看,更可以看出范晔史学的特点。
中兴二十八将论是针对旧论所谓“光武不以功臣任职。至使英姿茂绩,委而勿用”进行评论的。范晔把这种想法叫作“授受惟庸,勋贤皆序”的想法。他认为,这在春秋时期还能做得到,秦汉以后就做不到了。这一方面是因为开国功臣多是武人,权力过大了就会出问题:“势疑则隙生,力侔则乱起。”结果倒对功臣不利,会送掉他们的身家性命。又一方面是因为专任功臣,对吏治有碍,易于“使缙绅道塞,贤能蔽壅,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关之怨”。范晔并不否认“授受惟庸,勋贤皆序”更合理想,但认为,在秦汉以后,光武的“高秩厚礼,允答元功,峻文深宪,责成吏职”却更为切实可行。范晔在这里所表现的方法论上的特点是:在面临无法解决的矛盾的时候,要有所取,有所舍。只要这一方面的利益比那一方面的利益更大更重要,就算做得对了。他在《荀彧传·论》里把这叫作“功之不兼”,“有全必有丧”。他这样做法的好处,就是能比较多方面地看出各种不同矛盾,能比较具体地结合实际条件作出历史的论断。他所针对的旧论是跟袁宏的议论相同的,他的具有朴素辩证法的论点,在一些历史问题上,总是跟袁宏有很大分歧的。
《后汉书》中的赞是写得很凝练的,赞语时有新意,形式也富于变化。自《光武帝纪》至《献帝纪》的赞,概括了东汉建立、发展和衰亡等不同阶段的政治大事,把这9首赞合起来看,简直是一篇用韵语写的东汉政治史略。列传5至12记二十八将,其赞语,或合赞本卷各人,或专赞一二人,而列传12的赞语则是合赞二十八将的。《文苑传·赞》说:
“情志既动,篇辞为贵。抽心呈貌,非雕非蔚。殊状共体,同声异气。言观丽则,永监淫费。”
这是范晔发挥自己的文艺思想。《儒林列传·赞》说:
“斯文未陵,亦各有承。涂分流别,专门并兴。精疏殊会,通阂相征。千载不作,渊源谁澄?”
这就又是对专门经学拘守一隅之总的批评了。但赞文过简,语意费解。而辞藻虽美,内容未免笼统的情况也是有的。
4.无神论者范晔
从历史上看,范晔是一个无神论者。他的无佛鬼论是跟当时作为正宗思想重要构成部分的佛教对立的。
宋文帝有意以佛教来辅助统治。公元435年,他对侍中何尚之颂扬佛经是探求“性灵真奥”的指南,强调:“若使率土之滨皆纯此化,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
宋文帝时开始了关于佛教的有名的辩诘。《达性论》的辩诘和《均善论》的辩诘,就是以何承天、释慧琳为一方,以宗炳、颜延之为一方,环绕着因报有无、神灭不灭进行辩诘的。范晔跟何承天是同时的人,比后者早死两年。他“常谓死者,神灭,欲著无鬼论”,没有写出来。将要受死刑了,还“语人:寄语何仆射(何尚之),天下决无佛鬼。若有灵,自当相报”。他在临死前还对阴谋杀害他的这位佛教信士进行不屈的理论斗争。
范晔在《西域传·论》里,比较集中地批评了佛教。在一开始,他指出自张骞以来对西域的记载“莫不备写情形,审求根实”,但都没有写什么印度佛道的神化。后来关于佛道“理绝人区”的“神迹诡怪”和“事出天外”的“感验明显”,等等,都是张骞、班超没有听见过的。范晔问道:“岂其道闭往运,数开叔叶乎?不然,何诬异之甚也!”这是要从历史上指出佛教的种种说法都是后起的,因而跟张骞、班超所记的相比,就显得有很厉害的虚构和怪诞了。
“详其清心释累之训,空有兼遣之宗,道书之流也。且好仁恶杀,蠲敝崇善,所以贤达君子多爱其法焉。然好大不经,奇谲无已。虽邹衍谈天之辩,庄周蜗角之论,尚未足以概其万一,又精灵起灭,因报相寻,若晓而昧者,故通人多惑焉。”
这是说,佛教的玄理和修行为士大夫所喜尚,但它用的方法是诡辩的,它的神不灭论和因果报应论是没有道理的,这是“通人”所不相信的。因为文章简短,范晔没有提出充分的论证,但他集中了当时反佛的论点。他所说“贤达君子多爱其法”,并不是说佛法仍有其优点,而是讽制当时当权人物崇佛的微词。他所谓“贤达君子”是跟“通人”相对立的。
范晔在《桓帝纪·论》说:“前史称桓帝好音乐,善琴笙,饰芳林而考濯龙之宫,设华盖以祠浮图老子。斯将所谓听于神乎?”他在这里用了《左传》上的一个典故,批评了汉桓帝崇佛的荒谬。他在《襄楷传》载襄楷上书桓帝说:“闻宫中立黄老浮图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今陛下嗜欲不去,杀罚过理,既乖其道,岂获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爱,精之至也。天神遗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眄之。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淫女艳妇,极天下之丽;甘肥饮美,殚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黄老乎?”这篇话之收入《后汉书》,可看作是范晔对崇佛的“贤达君子”的讽刺。这些人也只是嘴上说说佛法,实际生活上是不能做到佛教戒律的要求的。
范晔不信图谶。他指责李通说谶是“亿则微隐、倡狂无妄之福”;指责光武以后“儒者争学图谶,兼复附以妖言”,是由于世主的崇尚。他既记载了桓谭所说“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其事虽有时合,譬犹卜数只偶之类”,又称“谭非谶术……体兼上才”。他在《张衡传》详细记载了张衡论图谶疏,这是从历史上揭露图谶欺伪的有力量的文章。
范晔不信阴阳禁忌。《郭躬传》附记廷尉吴雄,少时家贫,葬母不择茔地时日,“医巫皆言当族灭而雄不顾”,后来子孙三世为廷尉。记司隶校尉赵兴“亦不恤讳忌,每入官舍,辄更缮修馆宇,移穿改筑,故犯妖禁”,子孙也是三世为司隶。他又记一个反面的例子:陈伯敬禁忌多端,口不言死字,却不免被杀。范晔在记三人事以后,说:“时人罔忌禁者,多谈为证焉。”这可见他于史事记载中寓有破除迷信的意图。
《方术列传·序》是范晔对各种方术的总论。他在开卷述各种方术后说:“时亦有以效于事也。而斯道隐远,玄奥难原,故圣人不语怪神,罕言性命。”这在总的方面,表示的是一种保留态度。接着说:
“汉自武帝颇好方术,天下怀协道艺之士,莫不负策抵掌,顺风而届焉。后王莽矫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谶言,士之赴趣时宜者,皆骋驰穿凿争谈之也。故王梁、孙成名应图箓,越登槐鼎之任;郑兴、贾逵以附同称显,桓谭、尹敏以乖忤沦败。自是习为内学,尚奇文,贵异数,不乏于时矣。是以通儒硕生忿其奸妄不经,奏议慷慨,以为宜见藏摈。子长亦云:‘观阴阳之书,使人拘而多忌。’盖为此也。”
这就指出:方术之盛,不过是因为可用以逢迎世主以取禄位,而其奸妄不经是为通儒硕学所排斥的。这里也透露出范晔在对待方术的态度上,跟司马迁是一脉相承的。最后,范晔归结为:“夫物之所偏,未能无蔽。”“极数知变而不诡俗,斯深于数术者也。”他举出:“张衡为阴阳之宗,郎顗咎征最密。”这是他对于方术所表示的一种合理的态度。他所谓“极数知变而不诡俗”,就是肯定了方术的科学内容而否定其违背常识的迷信。他推重张衡,也就是按照这个标准来评定的。
范晔的无佛鬼论和反对其他神秘思想,都是他的无神论的内容。他虽没有系统地组织起来,但涉及的方面相当广泛,并且表现出战斗精神。
范晔也像中古的其他无神论者一样,不能把对有神论的战斗精神转向历史理论上唯物主义的建设。他在《马融传·论》说:
“夫事苦则矜全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虑深。登高不惧者,胥靡之人也。坐不垂堂者,千金之子也。原其大略,归于所安而已矣。物我异观,亦更相笑也。”
这指出不同的财产占有情况决定了不同的生活态度,并决定了互相背异的观点。范晔的这几句话表示他在历史理论上唯物主义的观点。可惜这样的话说得不多,他以杰出人物决定历史的看法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
5.袁宏撰集《后汉纪》
《后汉纪》是袁宏撰集众书而成。因东汉史的著述情况跟西汉史著述情况不同,袁宏所面临的著述本身的问题和受到的考验也都跟荀悦不同。当年荀悦著《汉纪》的时候,只有《汉书》是一部完整的西汉史,他剪裁了《汉书》就成为新的著作。此后,在很长的时期内也很少新的西汉史问世。袁宏著《后汉纪》的前后,关于东汉史的著述是有好多种的。在纪传史方面,有三国时谢承《后汉书》130卷,晋薛莹《后汉记》100卷,司马彪《续汉书》83卷,华峤《后汉书》97卷,谢沈《后汉书》122卷,张莹《汉南纪》58卷,袁山松《后汉书》100卷,宋范晔《后汉书》90卷,刘义庆《后汉书》58卷,梁萧子显《后汉书》100卷,连同东汉时官府陆续修撰的《汉纪》143卷,共11种。在编年史方面,有晋张瑶《后汉纪》30卷,习凿齿《汉晋春秋》47卷,孔衍《后汉春秋》6卷,连袁宏自己的《后汉纪》共4种。袁宏自述:
“子尝读《后汉书》,烦秽杂乱,睡而不能竟也,聊以暇日,撰集为《后汉纪》。其所掇会《汉纪》、谢承书、司马彪书,华峤书、谢忱(沈)书、《汉山阳公记》《汉灵献起居注》、汉名臣奏,旁及诸郡耆旧先贤传,凡数百卷。前史阙略,多不次叙。错谬同异,谁使正之。经营八年,疲而不能定,颇有传者。始见张瑶所撰书,其言汉末之事差详,故复探而益之。”
这可见他依据的资料要比荀悦繁富,遇到的困难和付出的功力要比荀悦多。另外,在同类著述上,袁宏遇到了不少的对手,这是荀悦著书时所没有的。最后,只有袁宏和范晔的书流传下来,司马彪书传下了八志,其他关于东汉史纪传、编年的著述都没有流传下来。
袁宏在《后汉纪》里表现了综铨史事的才能。他以八卷的分量写光武帝时期约40年间的历史。他以光武帝事业的发展作为基本线索,一方面写吕母、赤眉、新市、平林的起兵,王莽的失败,隗嚣、公孙述、李宪、张步、刘芳、董定、秦丰、王昌的自雄,又一方面写光武帝手下的名将如邓晨、李通、冯异、铫期、王霸(襄城人)、傅俊、马成、岑彭、坚镡、祭遵、臧宫、邓禹、耿纯、朱祐、贾复、陈俊、耿弇、任光、李忠、邳彤、刘植、寇恂、盖延、王梁、吴汉、刘隆、马武、景丹及窦融等的相继出现及其生平和功绩。这40年的历史,头绪多,人物多,错综多,在他的笔下写得错落有致。他以六卷多的分量写灵帝中平元年(184年)黄巾起义以来,董卓的当权、群雄的混战、曹操的得势和赤壁之败,以致曹魏代汉,这也是全书中写得详细、精彩的部分。
袁宏在《后汉纪·序》里提出了“言行趣舍,各以类书”的撰集方法。从实际运用上看,这比荀悦的连类列举要有些发展。苟悦有时也类举多事,但主要是类举一两事。袁宏总是把时代约略相近的同类人物连续地写出来好几个。如《后汉纪》卷五写了闵仲叔,又写了王丹、严光、周党、王霸(太原人)、逢萌,这都是以隐士终身或度过长期隐居生活的人物。卷22记处士,连续写了徐稚、姜肱、袁闳、韦著、李昙的事迹。这样的写法,扩大了编年史可能容纳的范围,但如使用过多,就不免随时出现人物小传或轶事的简单连缀,这就把编年的特点削弱了。在《后汉纪》里,这种优点和缺点都是有的。
袁宏运用“类书”的企图,主要是加深读者印象,要以某种类型的人物去感染读者。因此,他在《后汉纪·序》里提出了要达到“观其名迹,想见其人”的要求。可以通过“类书”,也可以通过别种方法,来达到这种要求。他批评那些注释家们对于《左传》的做法:“其所称美,止于事义,疏外之意,殁而不传,其遗风余趣,蔑如也。”他担心“今之史书或非古之人心,恐千载之外所诬者多”,因而感到“怅怏踌躇,操笔恨然”。他这样的要求曾为《后汉纪》带来了笔下传神的气氛。
比起陈寿来,袁宏表现了更多的文章家的才华,但缺乏一个历史家的审慎的态度。他更喜欢品题人物,有更多的清谈趣味,并且更公开地宣扬自己的观点。他在一部编年史里,很突出地重视历史人物才情风貌的记述,这是跟体现在他身上的这种世族名士的风尚不可分割的。他所以有时要在书内收入很易辨识的“附益增张”的“华辞”,也是跟这种风尚密切相关的。毕竟形式决定于内容,《后汉纪》的表达形式还是由阶级的剪刀和针线去剪裁和缝制的。
6.袁宏的“名教”观点
袁宏比过去的历史家都更强调历史记述的政治意义。他在《后汉纪》卷29删取荀悦《申鉴》近800字,在开头几句中就有“前鉴既明,后复申之”的话,在结尾说史籍的作用:“或有欲显而不得,欲隐而名彰。得失一朝,荣辱千载,善人劝焉,淫人惧焉。”从对《申鉴》内容的取舍上已可表现他对历史的劝诫作用的重视。在这一点上,他不满足于过去历史家的做法,其中也包含荀悦在内。他在《后汉纪·序》批评了历史学的前辈,公开地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说:
“夫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丘明之作,广大悉备。史迁剖判六家,建立十书,非徒记事而已,信足扶明义教,网罗治体,然未尽之。班固源流周赡,近乎通人之作,然因藉史迁,无所甄明。荀悦才智经纶,足为嘉史,所述当世,大得治功已矣,然名教之本,帝王高义,韫而未叙。今因前代遗事,略举义教所归,庶以弘敷王道。”
按照他的主张,历史著述的政治意义应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网罗治体”,“大得治功”,这是指政治上的得失说的。又一个方面是“扶明义教”,“名教之本”,这是指封建伦理上的是非说的。他认为,司马迁、班固和荀悦都做得不够。他的《后汉纪》就是要补前史之不足,重视名教的阐扬。“因前代遗事”,这只是手段;“略举义教所归,庶以弘敷王道”,这才是目的。
袁宏认为,“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他的论述重点常在于君臣关系。君臣关系是封建等级制度最集中的表现。他拿天地高下的自然现象和父子相继的血缘关系套在君臣关系上,把封建的君臣关系当作自然史的规律和永恒不变的真理。他说:“高下莫尚于天地,故贵贱拟斯以辨物;尊卑莫大于父子,故君臣象兹以成器。天地,无穷之道;父子,不易之体。夫以无穷之天地,不易之父子,故尊卑永固而不逾,名教大定而不乱,置之六合,充塞宇宙,自今及古,其名不去者也。未有违失天地之性,而可以序定人伦,失乎自然之理而可以彰明治体者也。”
袁宏也看到历史上的一些变化,并且还主张礼制上的改革。他曾指出三代历史上传贤和授子的变化、刑赏的变化、婚制的变化等,并说:“奕者之思尽于一局者也,圣人之明周于天下者也。苟一局之势未尝尽同,则天下之事岂必相袭哉?”他还指出文字记载在内容形式上的变化,说:“记载废兴谓之典谟,集叙歌谣谓之诗颂,拟议吉凶谓之易象,撰录制度谓之礼仪,编述名迹谓之春秋。”“然则经籍者,写载先圣之轨迹者也。圣人之迹不同如彼,后之学者欲齐之如此,焉可得哉?……风俗民情治化之术将数变矣。而汉初诸儒多案《春秋》之中,复有同异。其后殷书礼传往往间出,是非之伦不可胜言。六经之道可得详,而治体云为迁易无度矣。”他又说:“夫政治纲纪之礼,哀乐死葬之节有异于古矣,而言礼者必证于古,古不可用而事各有宜,是以人用其心而家殊其礼。”像这样的议论,是用一种历史态度看问题的,这在当时是难得的。在《后汉纪》50余条的史论中,有好几条这样的议论,都是值得注意的。但袁宏的历史态度也就到此为止,决不越过名教这一条线向前迈进一步。照袁宏的看法,历史上尽管有许多变化,但名教这条线是决不可动摇的。这就是所谓“尊卑长幼不得而移者也,器服制度有时而变者也”。
《后汉纪》对曹操的态度,显著地体现了名教观点在历史记述中的反映。
袁宏的名教观点也表现了他对客观历史的看法。他这样重视名教观点在历史记述中的作用,就因为他认为名教是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他在《后汉纪》卷二十二有一段论风俗的话,说春秋时“道德仁义之风往往不绝”;战国强弱相凌而游说之风盛;汉初“风云豪杰,崛起壮夫”,“徒以气勇武功彰于天下,而任侠之风盛”;元成明章之间“尊师稽古”而守文之风盛;其后宦官当权,“忠义之士发愤忘难”,而肆直之风盛。这也是用一种历史态度去观察风俗的变化。他指出的战国以后风俗的变化也是符合这一时期历史的一部分政治风气的特点的。他认为这些风俗虽有有益的一方面,但也有有害的方面,这都不是理想的。他理想的社会是:“野不议朝,处不谈务,少不论长,贱不辩贵。”这才是“先王之教”,这才可做到“天下有道”。
袁宏也相信天人感应,但表现的兴趣不如荀悦那样大。他会说:“神实聪明正直,依人而行者也。”这可以说是对神采取了保留的态度。
在《后汉纪》卷十,专有一段记述佛教,说佛“变化无方,无所不入,故能化通万物而大济群生”,说佛教“以虚无为宗,包罗精粗,无所不统。善为宏阔胜大之言,所求在一体之内而所明在视听之外。世俗之人以为虚诞,然归于玄微深远,难得而测。故王公大人观死生报应之际,莫不矍然自失”。这是第一次以正式记载的形式,称颂佛教而载入史书中的。东晋皇家自明帝以下,重臣自王导以下,多信佛教。这一方面因佛教的玄理,在时代的动荡中,结合传统的玄学,可望成为一种安定的麻醉剂,又一方面佛教的因果报应之说比儒家所宣扬的封建伦理更有麻痹人民的作用,从而佛教就逐渐挤入正宗思想的地位并得到不断的发展。袁宏是在史学领域里颂扬佛教较早的人物。他宣扬名教,又颂扬佛教,这正是一个正宗学者的特点,同时也反映了佛教的势力已经侵入史学的领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