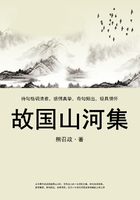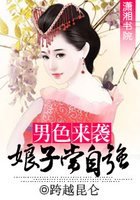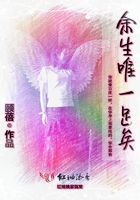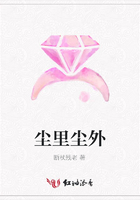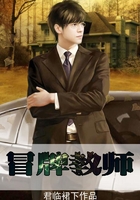薛忆沩,很高兴看到你的小说集《流动的房间》的出版。在中国,一位名气最旺的作家也要保持高产。夸张一点说,似乎一年不写一个长篇就不是作家。这种体制性的因素在你身上完全没有,你有数量的焦虑吗?
用“阶级斗争”的语言,你可以用“赤贫”来定性我写作的“数量”。小说集《流动的房间》是我用十八年时间完成的作品。我没有你说的那种焦虑。原因至少有两个:首先,我有太多其他的“焦虑”,比如对语言的焦虑。有时候一个副词的选择会让我彻夜难眠。还比如对时间的焦虑。我现在每天都需要时间来做运动,比如游泳一千米。如果有一天抽不出那四十分钟时间,我就会焦虑。这后一种倒有点像是“数量”的焦虑;第二,我从来就不是(或者不能是)一个专职的作家。我过去是教师,我现在是学生。我现在有许多学生的焦虑,比如刚写好的这一篇论文会得怎样的分数?我还有生理的焦虑,不知道人到中年了,为什么突然会“返老还童”,重新过起“小二郎”的日子。
我大概永远也不会成为一个能够靠写作“吃饭”的作家。这本来应该是我的“不幸”。万幸的是,这种无能并不会引起我的焦虑,因为我基本上是一个不要“吃饭”的人。我的意思是说,我对物质生活的要求极为肤浅,有时候会肤浅到令人喷饭的程度。
能够在今天这样的环境下出版小说集真是很不容易,所以大多数写作者更愿意去写长篇。据说目前我国每年出版长篇将近一千部,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很久很久以前,在还没有任何一家文学刊物愿意刊登我的写作的时候,我曾经说过一句逆耳的忠言。我说,中国文学如果想要有巨大的进步就要将中国的文学刊物关到只剩下一两家。我的意思是文学作品数量的泛滥对文学质量的提高只会产生阻碍的作用。现在,我对“供给”的数量已经不那么苛求了。我觉得每年出版很多的长篇小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供给”能够创造怎样的“需求”以及怎样创造“需求”。我在意我们每年出版的这些作品中有多少能够进入我们的大学教育体制,成为解读和批评的对象,成为文化传承中的一个节点。大学是文学的集散地。如果现在出版的作品不能够进入大学,这种“供给”就没有意义。《流动的房间》中的一些作品曾经进入过大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课堂,这是它们的荣幸。
现在,西方的出版也不景气。不过市场上每年总是会出现几起畅销的“奇迹”,同时那些不亢不卑的纯文学的“幽灵”也总是能够在市场的狭缝里顽固地出没。与中国的情况很不相同的是,这些“奇迹”和“幽灵”最后都能够进入大学的教学大纲,不仅影响到学生的学分,同时波及到未来的创造力及购买力。比如,《达·芬奇密码》很快就能够被大学教授链接到“骑士文学”的血脉之中,而那些不可一世的文学天才的新作也总是能够及时成为师生们咀嚼和切磋的对象。
你在国外学习英美文学,西方文学传统对你这样一个以汉语为母语的写作者有什么样的影响?
语言是世界上最神奇的东西。它是一种生理功能,大脑的功能。我大脑的配置比较落后,这是我的难言之隐。我曾经可以用法语写不坏的作文,但是,到了要用英语作文的时候,我却不得不将法语忘掉,将羞涩的内存腾给它历史上的宿敌。我不能够同时打开许多的“窗口”。
不过,我赖以写作的汉语依然保存完好。收集在《流动的房间》里的《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是我“背井离乡”之后的第一部作品。它的语言获得了那么多的好评。我两年前在一个访谈里恭维自己,说我的汉语依然能够“触及灵魂”。现在,我也不时清点一下自己的“语料库”。我很清楚,那里的一些词语因为时间的覆盖已经失去了光泽。但是,我确信我没有丢失任何的珍品。对于汉语,我需要的顶多是“除尘”,而不是“挂失”。
在文学上,我迷恋歌德的“世界文学”的信仰。向一切文学成就学习是一个热爱写作的人的道德和“法门”。这种迷恋令我受益无穷。有一天,我从一个英国人推荐我看的一位捷克作家的小说中读到一段关于十八世纪的书商的细节。一个神奇的句子出现在我眼前:“被查禁能够增加一本书的魅力,却不能增加一本书的智力。”这个句子本身显示了一种怎样的智力呵!在许多小语种的作品里,我们经常可以读到触目惊心的大智慧。
在我看来,你的作品是真正讲究叙事的。你总是给读者带来两个故事。一个是“关于”作品的故事;另一个则是作品讲述的故事。你不仅继承了二十世纪以来西方现代的叙事成果,又能够很好地将它与具体的中国历史和文化联系起来。所以你的作品不会让读者感到隔膜。在国内,不少人一直对怎么写和写什么争吵不休,你好像从不加入这种争吵。
谢谢你对我作品的评价。争吵起来我就会说不出话,这是我的“生理缺陷”。所以,我不会加入任何形式的争吵。这是“避短”,是一种务实的明智表现,而不是清高。“争吵不休”是没有意义的。其实,只要真的想写,时间就会告诉你怎么写。时间是最伟大的导师。
“怎么写”的根基是对生命的忠诚、对写作的狂热以及对语言的崇敬。收集在《流动的房间》里的许多作品都是在我与那些“什么”厮守了许多年之后才知道“怎么”写的。它们是“忠诚”、“狂热”和“崇敬”的结晶。我从来没有一劳永逸地知道过要“怎么写”。写作永远是“未完成的”。一个好作家不会相信自己彻底知道了要怎么写。“下一部作品”总是对每一个好作家的挑战和威胁。“向前看”总是会令一个好作家忐忑不安的。
非常喜欢你关于革命的几个短篇,如《首战告捷》、《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和《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我觉得这些作品对革命的残酷性表现得非常充分,对个人命运与历史命运的反差有深刻的领悟。它们与中国二十世纪以来所有的革命叙事都不同。
的确有不少人喜欢那些作品。关于革命的话题在我的文学世界中出现得很早。长篇小说《遗弃》的主人公图林就曾经创作过一篇题为“革命者”的作品,作为他7月22日的日记。《遗弃》的主人公是一个了不起的“写作者”,我从他那里学到了不少的东西。很可惜,他只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很可惜。为了显示对他的崇拜,我特意将他的一篇作品收集在《流动的房间》里:这就是《老兵》,小说集里篇幅最短的作品。在《遗弃》里,《老兵》是距《革命者》一星期之后出现的作品。它也是一篇关于“革命”的小说。与其他那些作品的主人公相比,《老兵》的主人公完全是“草根”。可是他对“革命”的领悟同样非常透彻。那是我自己非常欣赏的作品。
另外,在我完成于1989年1月,至今不能出版的长篇小说《一个影子的告别》中,“革命”同样是一个关键词。“影子”在叙述的链条上向与自己的“革命”密切相关的一个个人物“告别”,那事实上就是向“革命”告别。后来,在《今天》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评论注意到这部小说是“告别革命”这个后来在中国引起关注的话题最早出现的地方。小说从一个“革命者”的角度预言了一个重物质轻精神的时代的到来。这部小说的节选在《今天》杂志上发表过,但是,它的足本可能永远也没有机会在国内出版。
在中国,作者难免不摆出高高在上的姿态。他担心的是读者不明白,所以话要说满甚至说溢,八分的话说十分,于是作品的味道全部流失了。既不优雅也没有深度的作品,读者是不会满意的。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在我看来,文学是“文”与“学”的神秘结合。它受到许多古老的美学原则的制约。古典主义的节制始终是我诚服的原则。这种原则体现了对读者的信赖。
节制也可以说是一种“化简”。“化简”与“简化”不同。“化简”是对阅读的致敬,“简化”是对阅读的贬低。《流动的房间》可以看作是我诚服节制原则的一个见证。
节制应该是来自古希腊人对数学,或者更精确点,是对几何学的崇敬。数学是一切智力活动的基础,是审美的基础。数学告诉我们“多少”是足够的。这“足够”不仅仅是一个“数量”的概念,更重要地,它还是“质量”的保证。
听说你在学习用英语写作,你能谈谈这方面的体会吗?
我现在仍然是一名全日制的学生。去年我选了一门叫“小说形式”的课。那其实是一门写作课,选课的学生几乎每个星期都要用英语写一篇极短的小说,而期中要写一篇较长的小说,期末要写一篇更长的小说。在等待《流动的房间》出版的过程中,我就沉浸在这种“小说形式”里。我的老师是加拿大一位出名的纯文学作家。我很内疚我一直没有向她暴露过我与写作之间长期的“亲密关系”。她只知道她的这个学生每星期都会交来一篇优秀的作业,不知道这个学生在地球的另一侧原来是她的同行。
这门课给了我极大的推动。从我的第一篇作业开始,我的写作不断受到老师的表扬。老师表扬我故事的深刻、结构的精巧以及语言的细腻。这种不断的推动促使我完成了最后那一篇“更长的”小说。在小说中,皇帝问传教士是否能够发明一种仪器,帮助他记录下他的宠妃的每一个表情。那个传教士却建议皇帝学习令他不堪忍受的记忆术。这次写作让我“浅尝”了用英语写作的快感和艰辛。但是,我不知道我能够在这条道路上走多远。我希望我不要仅仅停留在一个皇帝对生命和爱情的困惑里。我希望我能够走得更远。
在你的作品里,我发现你对科学和历史都非常着迷。这是否与你的工科背景有关系?记得你谈到十二岁的一次阅读经历注定了你写作的宿命,你为什么没有直接上中文系?
几年前在伦敦遇见一位很有眼光的评论家。谈话中,他突然抱怨王小波的作品有太重的“理工科”色彩。我马上提醒他说我也是学“理工科”的。意思是,我的作品也应该遭受到他的批评。没有想到,这位评论家反驳说:“不,你的作品不同。你的作品很感性。”在他看来,我将文理的平衡把握得很好。
我的写作肯定与我的教育背景有关。我一直喜欢科学,我一直崇尚节制,我相信数学是美学的基础。但是同时,我的作品又是极为感性的,它们根植于我敏感脆弱的本性。
我没有学文科是一个历史的烙印。那时候,成绩好的学生都不去学文科。而到了大学,我终于成了成绩不好的学生。我的文学好像终于找到了存在的理由。
文理的分科其实没有必要那么粗暴。在西方,有不少人既写科普作品,又写纯文学作品。我也很想将来能够用汉语写出一些很受欢迎的科普作品。
现在回过头来看,你这种复杂的跨学科的求学经历对你的写作应该是有益的,还有你跨度非常大的生活经历。你怎么看待自己的经历与写作的关系?
我总是强调“生活来源于艺术”。关于生活,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一定会有比其他人更复杂的困惑,因为他能够同时生活在不同的时空里。记得博尔赫斯写的《博尔赫斯和我》吗?或者他为莎士比亚写的那篇著名的小传。一个艺术家其实已经没有通常意义上的“经历”。他的“经历”只是他人对他的简化。尽管我还没有完成或者永远也不可能完成我梦想完成的那部艺术作品,我却不愿意用世俗的逻辑去简化自己。
在我看来,我的经历没有什么“跨度”。十岁的时候,我最喜欢的公共场合是母亲单位的“图书室”。到了现在这充满困惑的“不惑”之年,我最喜欢的公共场合不过是升级成了形形色色的“图书馆”。我将近十八年的创作能够收集在这一本《流动的房间》里,也正是我的经历没有“跨度”的证明。我的生活始终围绕着印刷品。抽象点说就是围绕着“知识”。而用我总是对儿子唠叨的一句话就是:“一个人一旦被知识迷住了,他就永远成了一个无知的人。”
国内写作状况非常不稳定,大家都被这个消费时代催逼着,年轻人赶紧通过新概念作文比赛成名,老年人连忙重复出版各种文集以求不被文坛遗忘,正当年的则被出版社催着赶着出长篇,不顾市场的容量,动辄起印上十万。这种不正常的状况对作家的心态特别不利。像你这种“不入流”的作家还是更适合生活在“别处”,你应该庆幸命运的眷顾。
访谈开始,我们遇到了“写作”的数量。现在,我们又遇到了“出版”的数量。数量是我们这个数字时代无法逃避的局限。我前面说过,数量通常不是对作品价值的正确注解。
天文学上的数量是另一回事。“光年”的漫长和历史的荒谬一样,能够启迪关于生命的智慧。与无限的宇宙相比,一个特定星球上的一个特定国家中的一个特定行业里的一个特定品种的“数量”还有什么特定的意义呢?我有一次访谈的题目叫“面对卑微的生命”。我在那里谈到,如果一个人对天文学上的“数量”有所领悟,他就会理解生命的卑微,他就会心平气和地对待其他的“数量”。
我个人的情况可能有点特殊。我应该是一个不具备任何参考价值的“个案”。在“小说形式”课上写成的一篇小故事里,我的主人公与他的“阴影”在一个充满不安记忆的广场相遇。他的“阴影”问他为什么来到那里。主人公说是为了“记忆”。而他的“阴影”却说他自己来到那里是为了“遗忘”。从1987年《作家》杂志头条发表我的中篇小说至今,我有两次“告别”文坛的经历(第一次完全出于被迫)。这种经历告诉我,对一个注定的写作者,阶段性地被人遗忘或者遗忘自己不见得是一种很糟的生命状态。写作的生命有时候需要承受遗忘之“轻”。
其实,所有的人都是会被人遗忘的,这是上帝的“统筹安排”。而遗忘自己可能更是一种“超前的”消费。我庆幸自己能够享受这种消费,因为首先我在生理上不喜欢“热”和“闹”,同时我在心理上又很抗拒“热闹”。还有,我对生命的卑微有很深的认识。这种认识剥夺了我对别人的记忆的奢望。
现在,小说集《流动的房间》终于出版了。我不希望它成为保存记忆的工具或者开发记忆的“新产品”。阅读应该“眷顾”的是流动的房间里的“家珍”,那些兢兢业业的文本,而不是它们自惭形秽的“主人”。
后记
小说集《流动的房间》的出版是我写作生涯中的一件大事,它将漂泊不定的我带回到了文学的视野之中。这次的采访提纲由小说集责任编辑申霞艳提供。访谈原稿刊于2006年2月19日《深圳商报》“文化广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