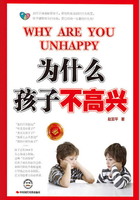下得山来,已是晚饭时分。
谈三的大妹和小妹鸭子婆正在楼前场地上跳橡皮筋,一个六岁,一个三岁。谈三一蹦几个高儿地过去,老气横秋地从脑后给两个妹妹一人一巴掌,惹得她俩扔下皮筋追着谈三闹,谈三甩了一大把鼻涕笑骂着进了屋。小Y刚走到那块大石边,就看见婶婶正站在门口台阶上,和共用一个台阶的一门洞的过太太说话。
婶婶不是多话的人。叔叔在湖大图书馆工作,婶婶在湖大一个缝纫社给人做衣服,赚几个钱补贴家用。小Y来此几个月,好像还没见过婶婶和邻居们在一起说话,尤其是过太太。这会儿两家女主人晤谈,看得出是因为同时在门口碰见了,属于不期而遇不得不说几句的场合。这过太太约模四十出头,先生是湖大的俄语教授,小Y见过一次,四五十岁模样,黑中显黄的头发十分熨贴地往脑后梳着,一丝不苟,且泛着油光。这种不寻常的发式常给初见他的人一个下马威,感觉像阿Q见了“洋鬼子”一样怪怪的。更怪的是过教授穿吊带裤,这令刚从小县城来此不久的小Y瞠目结舌。那次过教授也是站在敞开房门的门口送客,脚上竟然穿一双皮拖鞋,这在只穿得起自制布鞋、木拖鞋或回力鞋的邻居和常年当“赤脚大仙”的小Y们眼中更是不可思议。好在教授待人谦和有礼,送走客人后,见小Y还站在台阶一侧犯傻,他还特地冲小Y点头微笑。这给了小Y一个好印象。先生既不凡,夫人自不俗。过太太浓茂的黑发显然是熨烫过的,齐耳,在脑后隐隐呈波浪状,这在当时女人千篇一律的短直发型中明摆着就是个异类。细长的画眉弯弯的,秀气的双唇薄薄的;一件白色蕾丝的束腰上衣,配上绸质的黑色长裤,那在邻居们的腹诽中无疑是个“妖精”。过大少就是他们的大儿子。
正在门前台阶上说话的两家女主人看见小Y过来,婶婶就像得救兵似的掉转头喊:“悌伢子,何事(为什么)搞得咯(这)样晚才回来?”过太太笑眯眯地问:“是你侄子吧?”语音柔柔的,说的是长沙话,又带着些别的口音。不等婶婶回答,又冲小Y笑说:“长得咯样清秀,像个妹仔嘞!”婶婶也不接茬,冲小Y说:“就等你了,还不快进去摆桌子!”
平时折叠起,饭时才打开的红漆矮木桌,其实婶婶在前屋地上已摆放好,挨着娭毑平时坐的那张藤躺椅。裹小脚的娭毑那时七十来岁,除走路不便外,身体精神都还不错,一个人在家,靠看书读报打发时光。因小Y和老人家同在一室,这一老一小的感情就非其他血亲可比。娭毑在藤椅上坐好了,三岁的大弟弟早已乖乖坐在他的小板凳上。菜和汤上了桌,叔叔婶婶也从厨房过来落座,小Y给大家盛好了饭。
饭桌上,小Y和弟弟一如惯常地不吱声,事实上也没有他们细伢子说话的份儿。娭毑牙口不好,她的饭菜往往需要叔叔另作细软安排,叔叔在这一点上无可挑剔,孝子名至实归。叔叔是自学成才的烹饪高手,婶婶是尽职的助手。叔婶感情很好,他们之间的感情思想交流、生活信息传递多是在做晚饭的厨房里。叔叔四兄弟,可娭毑一直由叔婶侍候,婶婶有时嫌娭毑事多,免不了几句闲话,但叔叔恪守孝道,任劳任怨扮演着过去大家庭中孝子的角色。叔叔之所以在厨艺上有此一手,想来相当一部分也是为了娭毑吧。叔叔问“菜烂不烂呀”,娭毑答“还行,就是肉咸了点”之类的对话往往就是用餐的前奏曲。之后,娭毑有时会借此机会对儿子儿媳问点什么,吩咐点什么,叔叔就会说“晓得啰”。叔叔婶婶这时说得多点的也还是这顿饭菜做得如何,下顿做什么菜,要准备什么,等等。至于超出这个范围的话题,如叔叔在图书馆的同事如何如何,婶婶在缝纫社的人际相处怎样怎样,邻居们的家长里短,有的在厨房里也说了,另一些则大约是要到饭后收拾完一切,叔婶上二楼休息时才说的。但今天婶婶三言两语就说起了隔壁过家。
“那过太太还真是个时髦堂客。”婶婶边夹菜边说,“你看她和过教授穿的用的,以前怕是蛮有钱吧?”叔叔给娭毑夹一筷子菜,手指扶了扶眼镜说:“听得讲过先生留过洋噻,好像是个二级教授。”婶婶问:“那过太太也冒得工作,就靠过先生赚钱呀?你看他们好几个崽女,那得好多钱才养得起啰。”停了一会儿又说:“哎呀呀,还冒看见过咯样打扮的……”婶婶不说了,语气里流露着看不惯、交不起、不待见的意味。叔叔说:“莫管他啰,又不是一路人。”
在小Y朦朦胧胧的印象中,也觉得过家的衣着作派都有点“那个”,不过他对过太太并不反感,只是她把他比作“妹仔”叫他不大受用。不管怎么说,叔婶对过家夫妇还是有几分尊敬的,称呼他们为“先生”、“太太”,不像说四门洞主人——湖大的一位职员、独眼龙的老爸老妈为“老汪”、“汪家堂客”。至于谈三父亲,那个湖大的物理讲师,则被称为“谈老师”。叔叔没上过大学,与“老汪”同为湖大职工,他们为何会与过、谈二家同住这么一栋新洋楼,小Y就从未想过。
叔婶那时也才四十出头,因为没孩子,小Y父母遵照远在北京的嗲嗲(祖父)旨意,将大弟弟过继给了他们。他们对大弟弟自是呵护有加。叔叔不仅做得一手好菜,还通过家学渊源,通过读私塾,饱览典籍,攒下了一肚皮学问。他很早就戴上的近视镜度数同他的学问应是成正比的。因为在图书馆工作,叔叔不断借来各类书籍供娭毑浏览,自己则一上二楼就一卷在手。刚来乍到的小Y那时还沉湎在小人书和玩耍里,尚不知读书之乐也。但三岁的大弟弟晚饭后每每缠着叔叔要“听书”。“美伢子,咯回要听么子啰?”叔叔在唯一一张竹围椅上坐定,将弟弟抱置膝上,问。“还讲关公,还讲关公,上次还冒讲完噻!”弟弟回答得不假思索。“好啰!”叔叔翻着《三国演义》,他跳过弟弟听不懂的那些错综的人与事,直奔“三英战吕布”那一段开讲。
“……那吕布你晓得噻,长得武高武大,相貌堂堂,威风凛凛,武艺高强,骑一匹赤兔马,使一把方天画戟,有万夫不当之勇……”弟弟打断叔叔,认认真真地质疑:“那关公哩,你讲他是万夫不当之勇。”“关公是,吕布也是噻。”叔叔不紧不慢回答弟弟,“两个万夫不当之勇就要打起来哒噻……那吕布是奸臣董卓手下的大将,把守虎牢关。曹操领各路诸侯要破关,被吕布手起戟落,连斩几员大将。吕布东冲西杀,如入无人之境……搞得那十八路诸侯人人叫苦,个个胆寒!曹操只好和各路诸侯再商对策。就在咯个时候,吕布那厮又来搦战,冒得办法,再无大将可派噻,公孙瓒只好挥槊亲战吕布。战不几个回合,公孙瓒败走,吕布纵赤兔马赶来,看看赶上,说时迟,那时快,吕布举起画戟响起呼呼的风声,朝公孙瓒后背心就是一刺——”弟弟惊叫一声:“啊哟!”“莫急——就在咯千钧一发之际,燕人张翼德圆睁环眼,倒竖虎须,挺起丈八蛇矛,飞马大叫,‘三姓家奴休走!燕人张飞在此!’……”
叔叔说书的口才真是好,那抑扬顿挫的节奏感,说到两军对垒、英雄叫板时的面部表情、手势、语气,真把弟弟的兴味吊得足足的,他眼睛瞪得大大的,全神贯注,小手在围着兜兜的胸前紧紧捏在一起,还不时煞有介事地问叔叔:“那关公何事(为什么)不一个人跟吕布打啰……”小Y此时什么玩的念想都丢到爪哇国去了,叔叔讲说的三国豪雄们的音容笑貌、跌宕命运,以一种不可言说的力量整个攫住了这男孩的心。以至叔叔每说一段,次日他就要津津有味地复述给谈三和其他小伙伴们听,在这帮小把戏中也搅起了一阵“三国热”。
这些书想必娭毑也看过,虽然老人平日爱读的还是《红楼梦》《啼笑姻缘》之类,但每逢叔叔开讲,耳朵很背,身着长袍的娭毑也离开她的躺椅蹭过来,半个身子斜倚在书桌边,白发苍苍的头伸过来凑热闹,聚精会神地听,偶尔还要问一下小Y:“讲到么子地方啰?”
终于,弟弟的眼神有点迷离了,叔叔放下书,将他抱上二楼。此时婶婶晚饭收拾后,早早就上楼了,她每天凌晨五点就得起来给家里人准备早餐。过一会儿,叔叔又下来,像每晚必做的那样,问娭毑:“妈,该困得吧?”这是以往在营田老家那个旧式大家族中晚辈对长辈晨昏定省老例的延续。“你也去困啰。”娭毑一边宽衣一边说。同时也催小Y去睡。小Y此时正想从抽屉里把他点滴收集的小把戏搬出来玩一阵呢,听得娭毑说也只好上床。娭毑坐在床沿上开始往脑后扎她的白发,这意味着老人马上就要躺下了。但有时她会停下来跟叔叔说一两个婶婶的不是,譬如白天要婶婶给她做或买个什么的没做没去啦,婶婶因为什么事对她说话不恭敬啦,叔叔默默听着母亲的念叨,以一句“晓得啰”结束。
娭毑和小Y床上的帐子都放下了,但叔叔今晚并没如往常那样急着上楼,听脚步声,知道是去厨房了。屋里的灯还亮着。此时大约是九点来钟。不安分的小Y照例开始在帐子里折腾了,先是从枕头处抱膝一个跟头朝床尾翻过去,又从床尾一个跟头翻过来。如是十数个回合后,他又换了个玩法,因床是紧挨一面墙的,帐子也紧贴着墙,他就背靠墙,头冲下,窝着脖子,两肘撑腰,双腿高举,就这么倒立着,几分钟后放下来,接着又来几次,直到兴尽躺下。
可今晚小Y才翻两个跟头就无法继续下面的项目了,因为这时他听见一个声音从门外传进来:“Y夫子嗳,Y夫子在家冒?”紧接着叔叔的声音就从厨房那头一路传过来:“赵夫子来哒,快坐啰!”小Y床对面,两张高背西式黑木椅靠墙摆着,中间隔一高细木茶几,专供客人坐的。赵夫子落座,叔叔从厨房端出一碗刚蒸好的香肠片,一碟豆腐干,又拿来一瓶白酒,两副碗筷,坐下,两人就品上了。小Y虽直到现在不喜看书读报,却也晓得古代的“孔夫子”、“孟夫子”,知道凡“夫子”必定了得,可他不知道,他生活中也有“夫子”。其实这正是“惟楚有才,于斯为盛”,儒风遍被的结果。“夫子”之谓也,既是对对方的礼节性尊称,又是对彼“腹有诗书”的肯定和称颂。叔叔没正经读过中学,更别提上大学当先生了,但他端方的品格,饱学的谈吐,让他在同事们中间赢得了这个尊称;“赵夫子”想必也是。
他们在灯光下细酌慢品。这赵夫子是叔叔在湖大图书馆的同事。听得出来他们在说图书馆的什么事,接着又说起了这个书那个籍什么的,但折腾了一天的小Y突然间就睡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