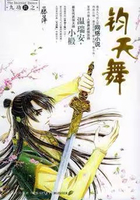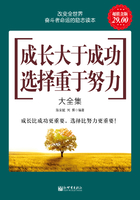毫无疑问,她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说这样的话,不只是她生了我的肉体,更源于这个如今日渐苍老的农村妇女一辈子不断践行的生活哲学——善良、勤劳、隐忍,甚至是开放而跳跃的思维——像精神的DNA一样,遗传给了我和我的兄弟。
母亲实在无比普通,作为这块土地上生活着的千千万万个劳动妇女的一员,养猪种地,烧火做饭,并没有超出日常生活的光芒,但因缘际会,她生了我,成了我的母亲,不但给了我肉身,还用她平凡的一生,塑造着我的精神世界。
这并不算夸张的描述。母亲某次来北京,是在夏天,她总和我们说:你们城里太臭了,走到哪里都是臭的。我当初不以为然,说:哪有啊,城里就是这个味道。她说:就是臭味。后来我才明白,母亲说的没错,在城里,你几乎闻不到清新的空气,遍布的下水道、垃圾桶、垃圾堆,还有人,把这个城市的味道变得很难闻了。然而每天生活在其中的我们,已经变得适应和习惯了这难闻的味道,反而是一个农村的老太太,凭着直觉和身体的敏感告诉我们,如果这就是城市的味道,那城市的味道就是臭味。
在农村,你随处可见农肥、牛粪、猪粪,但却并不感觉空气是臭的,因为所有的气息是整体,并有着自然的循环。在此之前,我从未真正闻到北京的味道,母亲让我张开了鼻翼,从精神上辨别出了城市和乡村的气息。我以这种方式回忆所记得的母亲的故事,也就似乎慢慢发现了她思维的轨迹,或者说,是生活的哲学。
1.
母亲比父亲大3岁,自结婚起,大概除了农民式的“婚姻式的爱情”,母亲对父亲还有些姐弟般的情感。正是这种情感,让她一辈子在父亲面前都处于弱势,所有的好吃的好用的,除了我和弟弟,她都给了父亲。结婚之后,父亲几乎过上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我5岁左右,父亲受四爷爷的蛊惑,到村里的小学做了民办教师,每月只有几十元的收入,且常常被乡里以各种名义扣掉。父亲还要在学校里吃午饭,有几年一年到头,不但一分钱不赚,还欠了学校几十块饭钱。这样的日子差不多有10年,都是母亲一个人的勤苦支撑全家,从春到秋,种田是她,薅草是她,收割是她,把粮食磨成面粉碾成米,最后做成饭的还是她。
母亲二十几岁时,我们还小,她也毕竟是年轻,自有年轻女人的爱好。有一年夏天,她日日早出晚归去挖药,两头不见太阳,两个多月断断续续上了30天山,终于攒下100块钱。她坐班车到乡里,千挑万选给自己买了一块表。这块表,她一戴就是20年,现在依然不舍得扔,存放在扣箱的一个纸盒子里——那儿都是些不值钱她却当宝贝的东西:我和弟弟若干年前写给她的信、我们小学时得过的奖状、幼年时的照片等。这块手表,成了当时年轻的母亲最大的财富。有了这块表,她再同村里的妇女们一起下田,自己多少有了些卑微的自豪,当其他人抬头看着太阳估摸时间的时候,她就抬抬手腕,说:“12点了呀,该回去喂猪了。”
年轻时的母亲,自然也爱美。有一阵子,二爷爷家的二姑从扎兰屯那边回来探亲,四爷爷家的四姑也从铅矿回娘家来。母亲和她们,以及村里相熟的几个妇女,整日穿得干干净净,相互串着门,一家一天轮流吃饭。不知道哪个提议,找人请了白庙子村的照相师傅,她们洗得清清爽爽,脸上擦了雪花膏,穿着鲜艳的红绿毛衣——虽然并不是穿毛衣的时令,但实在没有更鲜艳的衣服了——一起到南边的草场去拍照片。在我的记忆里,那几日的母亲,是她一生中最青春、最美丽的时刻。我总能记得当时的一张黑白照片:母亲坐在谷子地,紫红色的毛衣,头发卷着,戴一顶白色的凉帽,嘴角微笑,眼睛里荡漾着满足的神采。我很感谢照相师傅定格了这一刻,因为从母亲后来的生活往回看,几乎可以这样说:她生命里只有这短短的一瞬,泥土和庄稼不再是她的命运,而是背景,仅仅为了衬托她而存在。此前和此后,她都被土地紧紧地困着,在干涩粗粝的土块上站着、蹲着、跪着干活。
农闲季节村里人家都去山上挖药,赚几块买油盐酱醋的钱,母亲也去,总是步行,一天少说跑上百里。挖了几十年药,母亲唯一为自己买的东西就是那块手表。她从大山上背回的芍药、远志、黄芩、苍术,拎到村东头的供销社去卖掉,换回油盐酱醋,或者攒下来,等过年时扯几尺布,给我和弟弟做一身新衣服。等我和弟弟长到十几岁后,每年暑假也同母亲一起去采药,回来换下一学期的课本费用。若干年一直如此,那是我成长时的辛苦,也是我少年时的快乐。等冰箱这种电器开始蔓延到农村,村东的供销社和小商店里夏日总会卖些冰棍雪糕,我们兜售了药材,总渴望能买两根冰棍来吃,收入好的时候,母亲会给我和弟弟一人买一根。我们先给她吃,她只是象征性地咬一小口,说:“哈,真凉。”然后看着我们狼吞虎咽地消灭干净。几年后,我和弟弟都工作了,父亲也终于转为公办教师,家里的债全部还完,母亲再去山上采药,卖完之后终于可以放心大胆地买两根雪糕来吃了。终于有一天,她在电话中和我说:“这回吃足了,那些年真馋,舍不得吃,这回算是吃足了。”
和我一起上学的伙伴,都陆陆续续辍学了,去外地打工,在家放羊、种地,母亲却坚定地供我读书。当这些伙伴一个个给家里挣到了钱,或帮家里干了许多活的时候,我还只是父母看不见前路的负担。2000年,已经复读了两年的我,因为志愿填写不当,被大连的一所税务学校录取,我无法再拒绝这个大学,带着家里借的5000块钱只身去报道。可我心里一直有愤然和不甘。在那儿待了一个月,军训了一个月,忽然一天班长发下一个算盘来,我震惊不已,明白自己永远无法去当一个好会计,就想,我宁可去种地,也不要在这里浪费生命,便决定退学。
打电话给村东头的医生,让他通知母亲下午5点过来接电话,当时全村只有这一部电话。那天,母亲赶着驴车从地里往回拉玉米秸秆,她大概知道要发生什么,自己不敢去接,跑到学校找了父亲。下午,两个人到医生的小药房里,等着我的电话。我在电话里告诉父亲:“我要退学,不想念了。”父亲很愤怒,也很伤心,他无法理解其他孩子求还求不来的大学,我竟然不想念了。那一次,因为自己对命运的不忿,也因为想打动远在内蒙古的父母,我掉了眼泪。终于还是母亲心软,她在旁边和父亲说:“不愿意念就回来吧,让他回来。”父亲终于说了那句话:“你回来吧。”
我回来,在家里倒腾了一个月土肥。一天晚上,母亲说:“你还是再去复读一年吧。”其实,我一直在等这句话,只是自己万万没有脸去提起。我知道他们为我读书付出的辛苦与屈辱。母亲后来和我说,从我初中住校开始,她天天盼着我放假回家,可又怕我放假回家,因为每一次回来,总要带钱。有几次,她去村里有钱的人家里借钱,被冷言冷语顶了回来,就一个人躲在灶火坑前哭,哭完了想想不行,孩子还要上学呀,就抹一把眼泪,继续去求人、去借。那一段时间,家里甚至借过5分利的高利贷,每到年根,就会有村里人来家里讨债,母亲连忙沏茶、点烟,赔着笑脸,请人家宽限几日。事实上,那一段有不少亲戚家是有钱的,但没人愿意借出来,他们都不理解父母为何要拼死拼活供我和弟弟读书,觉得这钱借出去,可能就永远也回不来了。
2001年的秋天,我终于从学校传达室拿到北京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坐班车回来,半路车胎爆了,天黑才到村里。母亲一如既往地在村口等我,我下车,告诉她:“妈,我考上了。”她并没有喜极而泣,只是说:“考上了?好,好。”然后带着我到供销社买了几瓶啤酒,回去和父亲、弟弟一起喝了庆祝。第二天,一家人依然早早起床,套上车,去北山上拉干草。许多年的期待和折腾之后,考中大学已经不那么令人激动了,但无论如何,我知道母亲在人前人后的腰板挺得直了些,渐渐地,曾经被村人瞧不起的贫穷,竟然会隐隐地成为一种光荣。“看人家那么穷,都把学生供出来了。”读大学时放假回家,母亲常常要拉着我去供销社买点儿什么,最初我不爱去,后来我明白了母亲的小小心思,便和她一起出门,穿过其实很短的马路,再回来。母亲是想不动声色地把她的儿子展示一下,从村人略带羡慕的眼神里获得她这一生唯一能获得的小小的虚荣。
2.
小时候,兄弟两个皮实、闹腾,腿上像安了风火轮,手上没轻重,常常摔了碟子打了碗的。若是在正月,爹妈就说“碎碎(岁岁)平安,碎碎(岁岁)平安”,饶过一顿责罚。倘在平常日子,爹妈必定一顿严厉呵斥:“毛手毛脚,什么事都干不成。”然后将碎成几瓣的碟子碗小心收起来,静等着有一天大门外响起一阵悠长的异乡声音:“焗锅焗碗补水缸来哟……”将师傅请进院子里,把碎裂的碟子碗拿出来。师傅敲敲摸摸一会儿,说:“能焗,可是费功夫,两块钱。”老妈倒吸一口凉气:“赶上买只新的了,一块。”“一块五。”师傅说。“一块,送你两馒头一个咸菜疙瘩。”第二天,便有打了补丁的碟子碗端上了桌子,我和弟弟心中有愧,几乎不敢伸筷子夹里面的菜了。
2009年腊月,老弟从延边回内蒙古老家结婚,当时我就职的单位正人仰马翻地赶年前的活计,不能回去。所以在老弟结婚的那几天里,老妈都是通过手机给我现场直播盛况的。依照我老家那边的习俗,结婚要折腾好几天,提前从村里请了能烧大锅饭的厨子,十几个相熟的亲戚朋友做劳忙人(就是帮忙干活的意思),把和邻居家的墙拆个豁子,因为要在那儿院子里安排上几桌宴席。还有一件事顶顶重要,就是从信用社借上几百个碟子碗,自然是安排客人吃饭用的。
院子里用砖头垒起一个大灶,支上大锅,灶膛里榆木柴火日夜不停地烧:炒菜、蒸馒头、烧水。正日子那天,家里并上左邻右舍的东屋西屋都摆了桌子,早有支客(老家的音里读zhī qiě,就是招呼客人的大总管)按亲疏远近排好了一轮又一轮的座席时间。每桌有个桌长,负责倒酒散烟,劝同桌客人吃好喝好。众人就围坐了,忽然听得一声吆喝:“油着……慢回身……”是跑堂的劳忙人端着少说三个盘子过来上菜。然后七大姑八大姨互相攀着亲戚,灌着酒,品评红烧鱼和炖牛肉的好赖。大概一个小时,杯盘狼藉,迅速有人将碟子碗用大箩筐撤下,抬到井台那儿,一群大姑娘小媳妇用长满茧子或犹如葱白的手,分三遍将它们洗刷干净。不过十几分钟,这些碟子碗就又盛满了鸡鸭鱼肉摆在桌子上,迎接下一波客人了。
婚礼结束第二天,我又打电话给老妈,尽管对婚礼的诸多环节都很熟悉,可我还是作总结似的问了一句:“妈,他俩婚礼挺好的吧?没出什么事吧?”
“好得很,”我妈说,“没摔一个碟子也没打一个碗,顺顺利利。”
“没摔一个碟子也没打一个碗”,搞了十几年文字的我,彻底被我妈这句话给惊着了,我想象不出还有什么话,能比它更具表现力和说服力。她老人家说的是碟子和碗,但又不仅仅是碟子和碗,她的意思是婚礼上的一切:客人对酒菜满意、娘家对接待认可、亲戚朋友没挑理,也无人喝醉了耍酒疯,请来的客人都安安全全回了家……总之,这个婚礼按着理想状态开始和结束。
若干年来,我一直对日夜不停的灶火、跑堂的吆喝和流水线上的碟子碗念念不忘,这是老百姓凡俗生活里难得一见的狂欢。碟子碗是见证,几乎所有的婚丧嫁娶,孩子过百岁,老人过寿诞,它们都要叮叮当当地在不同人家的桌子上游走一番。这些粗坯烧出来的碟子碗,就这么飞入了寻常百姓家,把一户又一户的悲欢离合都盛满再清空,循环往复,乐此不疲。
在这样的流转中,母亲和村民们所追求的就是那“没摔一个碟子也没打一个碗”的和睦平安,对老百姓而言,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值得渴望的呢?
3.
现在的母亲,身体还算结实,但终归年龄越来越大,头发掉了许多,膝盖也总是疼。看着她日渐衰老,我不能责怪时间的无情,唯一可宽慰自己的是,日子不再那么艰难,我和弟弟都成了家,她的心,终于能从紧紧绷了近30年的状态中稍稍舒缓。母亲的天性,也才在她半辈子之后,有了释放的可能。我才惊奇地发现,母亲有着很好的语言天赋和老家妇女极少见的幽默感,她常常用一句简单的俗话,将我们苦苦经营的叙事解构掉。我们在镇子上给他们买了一台DVD机,还从北京带了正热播的几部电视剧的碟片回去,想让她和父亲没事的时候看。大家一起看《越狱》,说起电视里的谁谁怎么进监狱、如何冤枉、何等不公,我和弟弟甚至有点争论。母亲听了一会儿,突然说:“没别的,这些人就是命不好。”她这句话一出,我们竟然无法反驳,用农村人的观念来看,这句话已经解释了一切。
我出的两本书,都曾拿回家,本来只想做个留存。有一天母亲专门打电话给我,说:“你的书我看完了。”我本不曾想到她会读这种艰涩的文字,便随口问她感觉怎么样。“还行,”她说,“你撒谎撒得还行。”我心里笑了,她说得对,所谓的小说,不过是一种虚构。所谓的虚构,用农民的话来讲,也就是撒谎。
还有一次,我们从村西回来,看到路口停着一辆卖西瓜的车、一辆卖菜的车、一辆过路的汽车和一辆村里的三轮,我们都说:“怎么这么多车啊?”母亲赶着毛驴喊道:“快看快看,汽车开会了。”我暗自惊叹,不知道她是如何把一堆汽车转换到“汽车开会”这样的修辞。此后我常留心母亲的话,发现那些简单的世俗的话语里,有着潜在的伦理、强大的逻辑和表现力。也是从这一刻开始,我渐渐晓得,不该拿自己的眼睛去看她的生活,我努力尝试着用靠近她理解事物的方式去理解她,尝试着去对她的喜怒哀乐感同身受。这时候,母亲不再仅仅是母亲,她成了一个老人、一个孩子、一个实实在在的灵魂。
她依然不辍地劳作,几十年如一日,一个人侍弄着几十亩地,养七八头猪、30只鸡、20只鸭子、四五十只羊、一头毛驴,锅里做着饭,院子里种着菜,手里搓洗着衣裳。以我现在的生存能力,我始终无法想象,母亲是如何承受这些纷繁复杂而且繁重无比的劳作。她的手,是这一切的见证。我还从未见过有谁的手像母亲的手那样,除了坚硬的老茧就是裂纹,一到冬天,这双手一沾水就会针刺般地疼。我握着母亲的手,就好像握着她五十几年的辛苦,温暖而酸楚,老茧划着我的手心,粗粝如石头。而母亲不会想这么多,她会笑着舞动自己的手说:“这手多好,挠痒痒都不用痒痒挠了。”
当我明白农民的辛苦也就是他们的命运,便不像少年时那样为此悲悲戚戚,反而是从根子上看清楚,他们比所谓的许多城里人,活得更丰富。8月份回老家,母亲讲起前一年收割玉米的情景。她说:“别人家都是两三口人收秋,咱们家你爸上班,就我一个人,怕落了后。”我知道,阔大的田野里,一旦别人的庄稼都收完拉走,只剩下你家的戳在那儿,牲口就会来糟蹋,也说不准有缺德的人来偷。因为进度缓慢,母亲着了急,早晨早早起来,腰也不直地干到晌午,回家吃口饭,喂猪喂鸡,狠狠地睡上一觉。等太阳偏西,不那么晒的时候,她就关好门,赶着驴车下田干活。太阳落山了,她吃块干粮,喝口凉开水,就着秋天又圆又大的月亮,干一整宿。母亲在闲聊中随口一说,我脑海里却立刻显出了这个画面:月亮,黑魆魆的田野,一个人影挥舞镰刀,一棵一棵地把成熟的玉米秸秆割倒,从田垄的这头,到田垄的那头,循环往复,天也静,地也无声,只有玉米叶子哗啦啦地响。我感到一种劳动的诗意,也感到了劳动的辛苦和寂静。我想象着那一夜母亲的内心,也许除了身体的疲乏,她也体验到了与以往不同的感觉了吧。我可以肯定,那只是劳动本身,也是善和美本身,或者,就是人本身。
后来,母亲的这段话,终于在我心里生发成一篇小说《秋收记》,当然情节是另外一回事,但那田野中月亮下的荞麦田,那山峦的沉沉的阴影,却始终是这篇小说的主要基调。也因为这一场景,我把母亲看作了在泥土里写作的诗人。我自然清醒地知道,在这所谓的美和善中,头发白了掉了,牙齿松了,腿脚蹒跚了,腰弯了。我也知道这个充满诗意的场景,在母亲五十几年的辛苦劳作的时间里,实在是轻薄得不值一提,但我还是珍爱它,把它当成是故乡之所谓故乡的一点儿根本,当成我在外漂泊迷惘时找到方向的灯火。
4.
我们才从家里回北京没多久,有一天母亲突然打电话给我,她的声音听起来有些难过和委屈,我猜到一定是有什么事情。在我不停地询问下,她终于说了,前几天上台阶绊倒,把腿磕了,本来以为没大事,可正面腿骨前起了一个鸡蛋大小的包,走路都困难。我很着急,问她有没有去村东看看医生,她说去了,输了两天药水,可一点儿也不见好。
“赶紧去林东吧,”我说,“明天就去,必须去。”
“家里没人管啊。”她还是放心不下。
“没人管就不管。”我几乎是在吼,她终于同意了。
第二天,母亲坐班车到林东的一家医院,开了刀。她本计划第二天就回去,可因为瘀血一时清理不干净,需要每天换药、输液,只能留在那儿,一待就是10天。我每天早晚给她打一个电话,不是宽慰她腿伤,腿伤经过检查和治疗,我已经不太担心了,而是宽慰她对家里的惦记。她觉得自己在这儿,家里肯定鸡飞狗跳乱了套。不管我怎么阻拦,她还是比预期早两天回去了,好在腿伤已经没有大碍,半个月之后,彻底痊愈了。
又忽然一天,她打来电话,我细细听,口气里透着小小的开心和得意,知道大概是有了好事情。果然,母亲说她和父亲去山里打杏核了,卖了80块钱。我也很开心,因为母亲终于从腿伤的消沉中恢复了乐观。能跑到山上去打杏核,证明腿确实没有问题了。然而,接下来的十几天里,她几乎每天都上山。我又开始担心,问她在做什么,是家里要用钱吗?她笑着说,不是,家里有钱,只是觉得前一段治腿花了1000多块钱,越想越觉得亏,她非要把这钱挣回来不可。果然,杏核打到1000块钱的时候,母亲不再上山了。
自从我结婚后,每次打电话给她,她总会说过几天我去北京吧,给你们做饭去。我开始很傻,直愣愣地说:“你来了家里怎么办?你不是离开家几天都不放心吗?”过几天母亲又说:“儿子,你给我弄个小推车,我也去北京,卖烙饼羊肉汤去,一个月也能挣不少钱。”后来,我终于明白母亲的心思了,便和她说:“你来吧,来了我就给你弄个小推车。”如此前后设想一番,似乎这事就要变成现实一样。过一段就要重复一遍,她并不觉得枯燥,我也为自己能成为她幻想的一部分而高兴。因为我已然知道,母亲的这些话,只是她对自己生活的一种幻想。她年过半百了,一直都是土里来土里去,她也一定设想过和现在不一样的生活,她也一定有简单却无法实现的梦,我愿意顺着她的幻想,为她构造出另一个可能的世界,让她在这个世界里,实现所有的渴望。
母亲有她的顽固,母亲也有她的天真,母亲用她的行动和话语,为我展现了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哲学。30岁时,我才写第一首以母亲命名的诗,把它录在这儿,献给我和你以及她与他们的母亲。
母亲
从未对我说爱
你不知道这个字的许多含义
你说的是
谷物、牛羊和野草
是食物、鞋子和信
你爱着它们
而它们
是爱我的
全部时光都被打包
像割完的麦子
我来到城市
每一个清晨到夜晚,背着它
不觉得沉
也不思念故乡
我多么想
照耀我的那些光也照耀你
不,应该是
我多么想
自己也能发光
为着更弱小的微尘
母亲,如果你给我的一切
我都能还给这世界
这世界就能以爱命名
爱不是耻辱
是饥渴
像我最初饥渴你的乳汁
好吧,让我们相爱
太阳升起之前
让母亲和儿子拥抱
粮食和土地成熟
让一代人
爱另一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