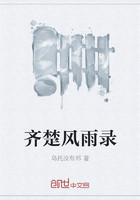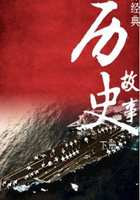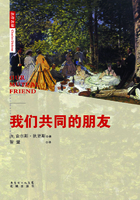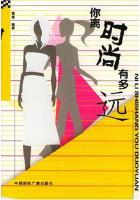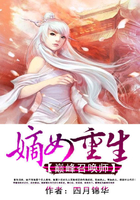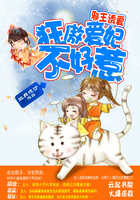《林石逸兴》是明代一部重要的散曲别集,共10卷,录曲1000首(按:今仅存999首,【仙吕入双调·玉抱肚】《乡思》佚1首),内容丰富,语言明快。
作者薛论道,字谈德(一作谭德),号莲溪居士,直隶定兴(今河北易县)人,生平难以确考。根据万历本《林石逸兴》所附诸人序跋中“万历庚寅(公元1590年)秋望,定兴龙川居士胡汝钦撰”“万历戊子(公元1588年)夏日,新安吴京书”“万历戊子孟夏上浣日,薛论道自述”“万历庚寅中秋日,永兴俞钟识于古檀青萍馆”等描述,知该集的刻成当不晚于1590年,其时薛论道尚在世。又结合集中“六十将近老形骸”(【双调·水仙子】《思归·其一》)、“屈指明春甲子周。六十后,四十秋”
(【仙吕·傍妆台】《自述·其九》)两支曲,可以断定他至少活到了60岁,则其生年当不迟于1531年,卒年则在1590年后。
据《定兴县志·卷十一·武功》记载:
薛论道,少婴沉疾,遇异人,针之,瘥曰:“当踦一足,然不琦不贵。”已而果琦。八岁能属文,试有司,辄冠军。亲没,家贫,遂辍博士业。读兵书,自负智囊,都下公卿呼为“刖先生”。许恭襄开府密云,辟为参谋。神堂峪有警,倡议利用寡不利用众,恭襄用其策,却敌十万众。叙帷幄,功授指挥佥事。万历初,戚继光镇蓟,建议弃黑峪关,论道白制府,力陈不可,状事竟寝,以是失戚意,移疾罢。久之,守大水峪,筑圈城于关外,人莫测也。后敌犯神堂,赚入圈城,歼敌无算,露布上,擢官三级,以神枢参将请老,加副将归[1]。
他幼年罹患重病,痊愈后一足终生残疾;天资聪颖,却因父母早故被迫放弃举业。薛论道一生最为人称道的,是以武将身份保疆戍边。《定兴县志》说他从军生涯的起点是被许恭襄公许论征辟为参谋。据《光绪顺天府志·卷七十三·官师志二》:
许论……(嘉靖)三十六年督蓟辽保定军务[2]。
嘉靖三十六年为1557年,许论是年开始镇守蓟镇等处,但不多时便被罢官,直到1559年才再度被起用:
公遂免。己未(公元1559年),敌大略滦西,上曰:“蓟辽督府务得人,朕欲仍用许论。”命甫下,欢声振边隅[3]。
因此,这是薛论道开始仕途的最有可能的两个时间。
综合各种资料,1559年或当更为可靠:首先,《密云县志》记载许论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任密云总督[4],这同《定兴县志》说薛论道在许论“开府密云”后才被征召吻合;其次,《定兴县志》提到的神堂之战,薛论道“倡议利用寡不利用众”的策略得到了许论的首肯,并由此成功退却了敌兵,有下列辅证:
(嘉靖三十九年)秋七月乙丑朔,把都儿犯蓟西,游击胡镇御却之[5]。
把都儿犯蓟西,论厚集精锐以待,至则为游击胡镇所破,遁去。事闻,厚赉银币[2]。
庚申(公元1560年),敌复把都既辛爱大举分略东西,公业已完缮停障,简练部伍,不遗余力,边百窥不得一间。入夏,不解春防。无何,伺大水峪……公登婢誓,诸军聚力战而却……俘首以闻[3]。
材料三中,敌分略东西,把都儿当率众进攻西路,而大水峪,参照明人郑大郁《边塞考·卷二·蓟州边图》,知其与神堂峪仅一河之隔[6],当属本次战役范畴。综上,薛论道的出仕最早当为1557年,更可能的则应是在1559年许论出任密云总督后。
隆庆初,戚继光北调,薛论道在黑峪关事件上同戚继光爆发了冲突。其时敌兵来犯,戚继光主张弃守,薛论道认为不可,理由是该处地理位置险要。戚继光也曾在隆庆二年所作《添筑黑峪关重墙》中写道:
曹家寨黑峪关去岔道仅四十里,最为冲要。外为雾露山,虽称险绝,但贼计奸狡,每每专伺险山不守之处,以步虏潜入,夺我关城,柝放大众入犯,此其故智也。而摩天岭墩至黑峪关仅数里,而近其山,俯瞰边墙如注坡,然正我所不意之地,实虏计所必通之途也。况墙内形险天成,逐墙可御……[7]
也许正基于此,薛论道才觉得有必要提醒自己的主帅是否应当对弃守的决定再加斟酌。而且戚继光在同年十一月《颁条悉边弊,申谕将士,以共图补报檄》中还对全体将士作过一番言说:
然倭盗情状与虏不同,南方山川与北殊绝,本府十五年前历戍蓟镇,而今日事体即求之往日,亦难比论,不能不深望于同事二三君子。本府虽极谫劣,然于虚心受善,克己闻过,二事仅可自信,傥如一切施行未当,愿诸同事直言无隐[7]。
其时他上任不久,单就文字看,可谓开诚布公。诚然,战场形势复杂,需要通观全局、因时制宜,但如此对待下属的意见似乎有欠妥当。我们不清楚中间究竟还发生了怎样的事情。这最终导致薛论道罢官归田,“或濬渠通漕以备军资,或治堤障水以活万姓”。薛论道复出后再立战功,以神枢参将加副将归老。
《林石逸兴》内容丰富。曲学前辈任中敏在《散曲概论》中总结散曲所能表现的内容时曾说:“以言人物,则公卿士夫、骚人墨客,固足以写;贩贾走卒,娟女弄人,亦足以写,且在作者意中,初不以与公卿士夫、骚人墨客有所歧视也。大而天日山河,细而米盐枣栗,美而名妹胜境,丑而恶疾畸形,殆无不足以写,而细者丑者,初亦不与大者美者有所歧视也。要之,衡其作品之大多数量,虽为风云月露,游戏讥嘲,而意境所到,材料所收,固古今上下、文质雅俗,恢恢乎从不知有所限,从不辨孰者为可能,而孰者为不可能,孰者为能容,而孰者为不能容也。其涵盖之广,固诗文之所不及。”薛论道不仅对上述内容多有涉及,很好地继承了前人的传统,而且亦有开拓。例如对军人形象的刻画、对军旅生活的描绘:
荏苒又重阳,拥旌旄倚太行,登临疑是青霄上。天长地长,云茫水茫,胡尘尽扫山河壮。望遐荒,王庭何处?万里尽秋霜。
【商调·黄莺儿】《塞上重阳·其一》
计而后用,利而后动。须知八战八克,更想七擒七纵。看他每智术,百发百中。多谋韩信,有勇重瞳。可怜举鼎拔山势,却被缚鸡饿殍倾。【仙吕·桂枝香】《智将》
雄威一奋,天摇地震。挥戈百万成泥,跃马三军如粉。闻霹雳弓声,电驰雷迅。虎踏羊垒,鹘荡鸦群。摧锋陷阵称绝技,挝鼓搴旗更有神。【仙吕·桂枝香】《勇将》
而像以书斋寄托相思:
目秦云楚云,送残春晚春,蝶乱飞花成阵。新来是睡昏昏,诸事无心问。笔砚慵亲,诗书懒近,人儿心头印。减尽精神,费尽殷勤,盼不到传信。【中吕·朝天子】《书斋·其一》或将儒家倡导的“仁”“义”“礼”“智”“信”等理念以单支散曲予以重点阐述:
探人之立身,最先乎立本,兴孝弟怀忠信。循循勉勉力于仁,知务者须当尽。三月不违,五常不紊,在邦闻于家训。仁者安仁,智者利仁,在君子无不慎。【中吕·朝天子】《仁》在前代曲家笔下也较为罕见。
艺术上,薛论道的散曲也多有“看点”。例如篇制方面,他的曲作全为小令,只用10种曲牌,且“联章”体比例惊人,占到了全部作品的77.4%。修辞方面,他善于运用“合璧对”和“扇面对”,喜用“暗喻”和“借喻”,敢于大胆夸张。章法方面,他倾向于以“开门见山”的方式快速切入正题,中段部分的铺写则较为集中地使用“抒情”与“描写”的方法,曲末又多“以情结尾”,使得曲作由简洁、晓畅、自然往内涵深处过渡,既顺应了散曲文学的规律,又符合读者接受的实际,同时产生余味无穷的效果。但是有些散曲议论、说理占据了不小的比重,使得作品又带有较为浓重的说教色彩,与传统意义上的散曲文学相比产生了一定的异变。这些,使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
《林石逸兴》刻成后久湮不闻,其版本如今可见者约有四种:
1.明万历十八年原刻本。今藏北京国家图书馆,框高199毫米,宽288毫米,白口,四周双边,每页10行,每行18字,内容顺序依次为胡汝钦《林石逸兴序》、薛论道《林石逸兴序》、目录、正文、俞钟《跋林石逸兴》和吴京《林石逸兴引》。这是《林石逸兴》最早、最完备的版本,除了卷十【仙吕入双调·玉抱肚】《乡思》8首佚1首外,基本保留了当初刻印时的原貌。《续修四库全书》据此版本影印。
2.卢前《饮虹簃癸甲丛刻二十种》所收版本(下简称“饮虹簃本”)。这是卢前于1936年根据他所见《林石逸兴》的一个残本刻印而成,仅收录卷一全部以及卷三的前29支曲。该版本每页10行,每行17字,内容顺序依次为胡汝钦《林石逸兴序》、吴京《林石逸兴引》、薛论道《林石逸兴序》、卷一目次、总目录、卷一正文、卷三目次、卷三前29支曲、俞钟《跋林石逸兴》以及卢前的跋语。卢前在跋中说还见过一个“第二卷及第九、十两卷阙”的版本,可他并没有照此版本重印,该版本现在也无从查寻,甚为可惜。饮虹簃本我可以说是《林石逸兴》的最残本,其价值更多体现在校勘方面。1980年,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曾根据民国版重印。
3.《故宫旬刊》本。该版本亦自言是根据第二、九、十卷阙的残本著录,然而最终也只刊录了卷一及卷三的前29支曲,但文字和“饮虹簃本”多有出入。内容顺序依次为胡汝钦《林石逸兴序》、薛论道《林石逸兴序》、俞钟《跋林石逸兴》、吴京《林石逸兴引》、总目录、卷一目录、正文、卷三目录及卷三的前29支曲。
4.《全明散曲》本。这是目前最常见的一个本子,也是绝大多数散曲研究者的工作底本。
在中国古代散曲史上,薛论道是存曲最多的作家,因此对其散曲集进行校注,是很有意义的。本书以《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明万历刻本为底本(下简称“续四库本”),以谢伯阳《全明散曲》本为校本(下简称“谢本”,在“校勘”中不再注明),同时参校“饮虹簃本”和《故宫旬刊》本(下简称“旬刊本”),于文字相异处出校记。可确定正误者,皆注明原因予以判断;难以辨别者,提出观点,或仅著录差异,兹供参考。诸本皆虚缺的文字,以“□”标示。在文字注释中,我们参阅了大量工具书,限于篇幅,不一一列出。一些文字则保留了古书中的用法,未作改正。
在校注过程中,我们虽谨小慎微,力求尽善尽美,但限于学识和经验,书中疏漏在所难免,望读者不吝赐教。
【注释】
[1]定兴县志.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200号[M].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69:548-549.
[2]光绪顺天府志.续修四库全书·第685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46.
[3]灵宝县志.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491号[M].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573.
[4]密云县志.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139号[M].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68:207.
[5]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246.
[6]边塞考.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第26册[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590.
[7]戚少保年谱者编·续修四库全书·第553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