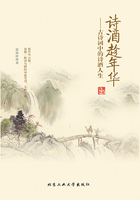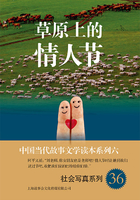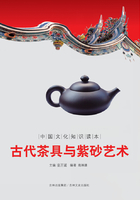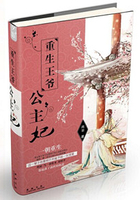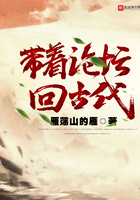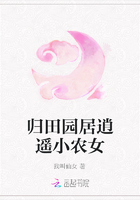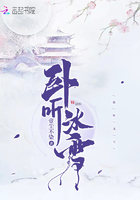2011年8月份,我和大陆几位新闻同行前往台湾进行为期10天的交流。当时没怎么注意一些细节,比如去到台北以外,住的全是乡间小木屋。回想一下,那应该是最正宗的民宿。
周边居民是当地村民,房舍一应为日常布置(除了更干净些,多通铺),像极了现在大陆流行的青年旅舍。
对应大陆目前的各种乡村精品酒店,这种民宿更居家,也更有生活的意味。我想,对来止溪的朋友来说,不应该是花钱来买某种东西,而是提着礼物来看望朋友。
有关台湾,印象最深的,其实是他们的公共生活方式。
8月13日,我们被带到阳明山,体验新形态的休闲方式——工作假期。
这也可以看作一种志愿者活动,工作内容是穿着青蛙装在一片水塘里将那里疯长的外来物种给揪出来,销毁掉。
看来,外来物种的大规模入侵,在全球化背景下,在各个地方都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主办方提供了工作用的各种工具,以保证即使没有专业知识背景也不会出现意外。
活动结束后,每个人谈了对环境保护的感想,以及对这种工作形式的建议。活动主办方领导签字后,给各位参与者颁发了活动证书,以示对各位参与者的感谢。
这个活动对我触动很大。其实一开始,对于从农村出来的我来说,这样的活动是缺乏吸引力的,但是活动结束后的感想以及纪念的方式让人对活动的意义和价值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回来后不久,房子还没踪影,我先让朋友设计了同款证书,以发给将来到止溪参加生态建设的朋友作纪念。
屏东县来义乡住着排湾族,那里是遭受八八风灾最严重的地方之一。灾后重建,并不是政府一夜之间建立起安置房,而是着眼于文化的复兴和重构,使得来义获得另一种新生。
毫无疑问,老一辈的山地民族,在城市化过程中被抛弃,成为弃民;新一代的山地青年,早已进城合流。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村是没有未来的。
我们拜访了当地的部落头领。在当地务农的少数民族青年带我们进行了渔猎活动,但这其实已经类似于观光了。
当晚会开始,大家拉起手开始跳当地的舞蹈、劝酒时,才发现村里人并不少。但当晚会结束,我们惊异地发现,人们一群一群地去了其他村。原来,一个村已经办不起一场活动,只能几个村合伙举办。
与大陆一些农村的情况相似,历经大规模的城市化之后,台北这样的大都会集中了台湾大部分的人口,而浊水溪南边的农村,实际上已经空心化。
正因如此,在灾后重建时,出生和生长于当地但现已在都市工作的青年人,开始回流到农村,进行乡村社区重建。他们并不是着眼于物质的救灾,而是着眼于民族和地域文化的复兴。一场灾难,将他们同情的目光吸引回了故乡,并推动故乡的再生。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均是再生的结果。
有些好动的青年与当地的姑娘跳起了迪斯科,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无他,大家都已都市化。这一代青年,是拯救乡村文明的最后一代人,他们能够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搭建起对话的桥梁。等这一代人也故去,乡村将在主流文化中消失,不复存在,就像从来没有存在过那样。
如此观之,我们这一代出身农村的青年,是否有对乡村的另一种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