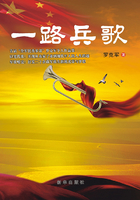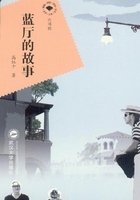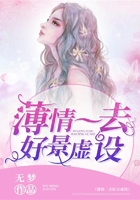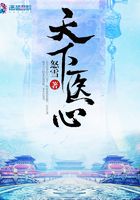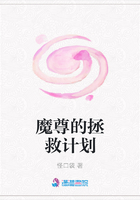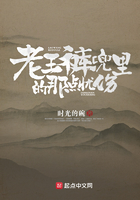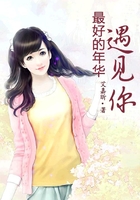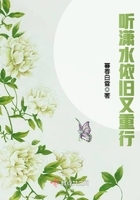9月19日,临近中午时候,我接到了大姐的电话,当即预感着一种意外。果然,大姐告诉的是尊敬的长辈昌翰先生(马谷中老师)在清晨去世的不幸消息。虽早有预料,也有心理准备,因为先生今年以来一直与病魔顽强地抗争着,可噩耗传来,仍悲从中来,十分痛惜。
第二天一早,我急匆匆地赶路,向着村里行进。往日时时感觉到的蔚蓝的天空,青翠的山野,清澈的溪流,这个时候,却觉得天色凝重,云雾低垂,青山含悲,清溪呜咽,仿佛这山山水水啊,全为失去一位敬爱的尊长而沉浸在无比的悲伤之中。
与先生同村,但少时并不相识,因为两家居住有一段距离。村子依山而建,先生住在村口附近俗称“下角头”,我家住在“上角头”,又称“城隍山”,更因为年龄和辈分上的差别,与先生不熟悉也属正常。只知道被村里人敬称为“翰老先生”的这位长辈在外教书育人。与先生相识并开始交流是因为大姐成了先生的儿媳妇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先生相处的增多,这位长者日益让我起敬,而且在亲戚之外,有了一种忘年交的意味。
那一年,极为重视教育的父母,不希望我早早放下书包跟随他们从农,鼓励我去更优质的学校读书。于是请先生向当时担任长乐中学教导主任的马尚骥老师推荐。先生与尚骥老师同为小崑村人,都是教坛名师,又情深谊长。尚骥老师欣然接纳了我,让我有了去这所名校读书的机会。先生不知我的名字由那两个字组成,凭主观臆测向尚骥老师报了名。在尚骥老师的笔下就成了这个名字——“马立远”。这大概是两位老师想象中的,也共同认可的名字。于是,我“将错就错”地采用了这个名字,直到现在。
每逢学校放假,回到父母身边时候,大姐家独具风格的三层洋楼便是我的快乐天地。当先生从嵊县师范学校教导主任岗位上退休回老家后,就有了与先生更多交流的时光,更有伯母的盛情款待。偶尔也会随先生到庄稼地里一起干活,在劳动的间隙里,坐在地角边小憩,面对着蓝天白云下的青山绿水,先生会讲述许多与教育有关的故事,不少是先生亲历的往事。虽是笑谈过去,可也流露着几多遗憾,当然更多的是坦然和乐观,特别是对年青一代的厚望。先生说三十年代末求学于嵊县县立初级中学,四十年代初,以浙江省第四名的成绩就读于丽水碧湖省立临时联合高级中学。在1942年春季高中毕业准备秋季报考西南联大时,却逢日寇入侵,在家滞留三年。1945年在缙云报考英士大学,因试卷泄密,考点作废,失去了上西南联大的良机。因为十年浩劫,天智过人的儿女也失去了上高中和大学的机会。在先生心里,这些都是平生憾事。可喜的是在新世纪的第一年,先生的孙子,即我的外甥志雷考取清华大学之时,先生喜不自禁,赋诗抒怀:“日寇文革机遇断,两代大学梦未圆。孙儿胸怀坚强志,高考录取清华园。”
先生从1946年开始教育生涯,虽命运坎坷,饱经沧桑,但一生追求真理、矢志不渝。先生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从教三十七年,桃李满天下。先生曾在三界中学、天台师范、嵊县中学、嵊州师范学校、嵊县教师进修学校等知名学校任教,并担任教导主任、校长等职务,也曾是嵊县政协委员。先生才智过人,教导有方,又诲人不倦,为人师表,深受师生的敬仰。
先生更是一位仁慈的长者,退休回乡后,热心公益事业,专门为村民讲课,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讲授伦理道德,传授科普知识,传播先进文化,这让村民大长见识,更对老人敬佩有加。一些父老乡亲在听课后,深受感动,他们遇上大姐时说:“你们一家儿女呀,应更孝敬先生,别怠慢了老人家。”为让村里的老人老有所乐,老有所教,先生热心支持利用凭依寺场所筹建老年活动室。那“老年之家”四个颇见功底又倾注感情的大字,即为先生亲笔所题。
先生健康时候,我常常坐在老人跟前,与老人细聊许多的话题,深受教益。先生生病时候,也会赶到老人病榻前,忧心如焚,更祝愿老人早日康复。先生珍爱生命,珍惜人生,虽经常住院,但总充满信心。近年住院次数增加,也几次病危,但老人总能坚强地挺过,转危为安。只是近年眼睛因白内障,几乎失明。夏天时候,先生在又一次病重住院回家后,我坐在先生的病椅前,倾听着先生诉说心愿:希望再活几年,还要去做白内障摘除手术。这就是渴望健康,珍惜人生的一位执着的长者,敬爱的长辈。
曾这样想过:家有先生,应备感自豪;村有先生,更应视为宝贵财富。现在,更想到了孟子的话:“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却觉得敬爱的昌翰先生真的有着这样的胸襟和情怀。
西白巍峨,碧水长流。先生已去,可精神长存,风范永在,一定会激励后辈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不辜负先生的期望。
(写于2009.0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