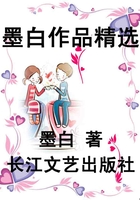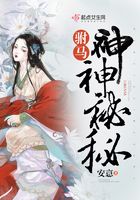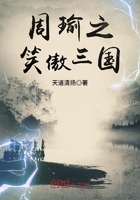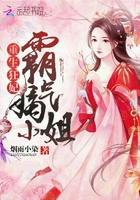我们家落户在外祖父的祖居地上。外祖父姓左。我们村的村名叫桂庄。
相传很早以前,在我们家乡一带,地广人稀。到了16世纪的明朝中叶,由于封建统治相对稳定,封建经济长足发展,人口不断增加,很多家族便不断向此地迁移,插草为标,抢占地盘,开荒垦殖。我们的村庄就是桂氏家族的一个院落。传说桂氏宗族在此一带很有势力,拥有大量财富,将桂庄建成一座花园,四面筑起围墙,村子中间建成牌楼、庭院,村前开挖一口长100余米宽40余米的椭圆形池塘,塘内植藕。盛夏时节,荷叶碧绿田田,粉红色的荷花绽放,露出鹅黄色的莲心,荷塘清香阵阵,风景煞是喜人。
到了明朝末年,桂氏家族的财富更多了,他们便打算大修祠堂以光耀桂氏门楣。可桂氏这一族祖上没有人做官。按照封建法典,修建祠堂有许多严格的规定,其中有一条最能反映家族荣耀和家族势力,即此家族中有人曾做过怎样的官职,祠堂就可达到怎样的规格。皇族的祠堂可建黄色龙饰,做过七品县官的家族祠堂可以起脊,可祖上未做过官的,祠堂只能建成平脊,不可装饰。桂氏为了光耀门楣,便用财产换取了左氏的一顶官帽,财产中包括桂氏花园及周围的田产。
当时正是左氏在朝廷中显赫的朝代,左光斗在朝中做着大官,深受皇上的宠幸,左氏一门兄弟九人都做着官。桂氏提出请求后,左氏便答应了,桂氏庄园从此便换了主人,归左氏所有,我外祖父的祖上便搬迁到这里。为纪念这件事(这也是左氏祖上的荣光),村庄的名字仍叫桂庄,村庄后面由天南山山脚延伸出来的小山便取名叫官帽山(喻村庄用官帽换取之意),庄名和山名一直延续到现在。
庄子的规模原先本不大,只有左氏几户人家。到了近五六代,祖上有一位姑娘嫁给菊氏,菊氏由于某方面的原因便搬迁到桂庄,居住在村子的东边。不久庄子西边又迁入了竹姓人家……村庄渐渐融合,到我出生时,已有几十户人家,两三百口人了。
祖上的事情很难追溯了,只知道外祖父的祖父是个手艺人——木匠。在过去的年代,手艺人在贫困的农村、在当地,是有一定声望的,脱离了庄户人家的范畴,十分受人尊重。外祖父的祖父虽然自己就是个手艺人,却叫自己的儿子拜别人为师学瓦匠。
拜师学手艺是件不平凡的事,须家里有一定的经济,一定的声望,一般人家是学不起手艺的。家庭没有背景,也无人肯收你为徒。拜师时你须在父母和族中有声望的人的带领下,先下拜师礼,向师父行三拜九叩大礼,然后办酒席宴请师父和族中有声望的人,师父庄严地宣讲行中的“清规戒律”,徒弟须万分恭敬地答应遵循,师父方可正式接受你为徒。然后便是学徒期,一般至少为三年。第一年,师父做,徒弟干些杂活;第二年,师父叫徒弟打下手,练些基本功;第三年才正式教徒弟手艺。学徒期间,徒弟须像对待父母一样侍候师父、师母,须帮师母带孩子,给师傅、师母铺床叠被子、倒马桶夜壶、干家务杂活,动辄还要遭到师父的毒打,平时学手艺时不得乱看乱问、乱开笑脸,吃饭定量,不得将肚子吃饱,干活没有工钱,每年还得敬上师礼。但到学徒后期,师父便对徒弟越来越尊重,越来越礼貌了。出师后,徒弟便单立门户,但“一日为师,终生为师”的古训在我们农村是很讲究的。
老外祖父(外祖父的祖父)特别聪明,听村里的老一辈们说,他拜师后不久便被师父辞出来了。原来老外祖父脑子特别活,什么瓦匠手艺看一遍就会。有一次,有户人家请师父去修灶,师父因手上活正忙便推辞过几天再去,而只看过师父修过一两次灶的老外祖父却自报家门说自己去试试。师父很生气,一个刚入门的小孩子不该如此不懂规矩、如此狂妄,但为了教训他,杀杀他的傲气,师傅便含讥带讽地说:你去把灶修好!想不到的是,老外祖父是个有心人。他来到灶前,一边拆心里一边记着灶上的土坯原先摆放的高度、角度和位置,然后依着原来的灶基竟将灶修起来了。
师父很没有脸面,便来到老外祖父家,含讥带讽地对老外祖父的父母说:你家的孩子,我没有本领教。坚决地将老外祖父辞掉了。父母无奈,而老外祖父便从此在外独闯了。
这是传说,真实的程度很值得怀疑。在我们乡下,为夸赞一个人,乡民是不惜夸大其词的。但在老外祖父的手艺生涯中有两件事经常被当地人所津津乐道。
一件事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在我们村庄山背面北方的瑜公乡,王姓的人家修建祠堂。瑜公乡属枞阳县,据说是三国时吴国大将军周瑜在此屯兵而得名,属枞阳、铜乡、江县三县交界的地方。王氏修建祠堂,除请了本地的手艺人之外,还请来了江县的一班手艺人。这可惹恼了当地的手艺人。手艺人是有组织的,即行会,行有行规,自古以来即如此。行会对如何授徒、定工钱、手艺范围、如何到范围以外做事等都有严格的组织和统一规定。这次江县人到我们范围内抢活,必须将他们赶出去!但客人是主人家请来的,不能硬性将别人赶走,必须在手艺上胜过他们,让他们灰溜溜地滚走!
他们较着劲,从工程开始到工程的主体,再到祠堂的雕梁画栋等全部完工后,双方还是不分上下,最后在祠堂门前要安两个石狮子,主人便让两班手艺人各造一个。这是很平常的活计,可老外祖父却在这上面动了脑筋。等到安装时,只见江县人雕的石狮子面朝前方,一副平常的样子;而由老外祖父设计的石狮子却面朝内侧,竖眉咧嘴欲扑向江县人雕的石狮子。这一气势立即压倒了江县人,他们自感技不如人,不该侵犯别人的地盘,便连工钱也不敢结算,急忙地逃走了。
另一件事是老外祖父在九华山上建庙宇。去九华山建庙宇的人没有过硬的手艺和过人的胆量,是不敢去的,行会也不会派你去的。来此建庙的都是各路的好手,他们在陡峭的石壁上开工建筑,随时都有掉下悬崖而丧命危险。
有一座临峭壁的庙宇建好了,却无人敢上屋顶盖瓦,因为盖瓦时,屋面很光滑,手又没有扶的地方,而屋下即为万丈深渊,人很容易禁不住头晕目眩而掉下万丈悬崖。人们犹豫着,有人用激将法对老外祖父说:“小左师傅,你行!等你盖成功后,我们将上梁的两条糕都给你。”
在乡下,在从前的时代,糕是吉祥、长寿的象征。乡下人在房屋即将落成,安放当顶处最后一根横梁时(这是大事,农村称为上梁,意思是房屋已建成功了),总让手艺最好、德行最高的一位木匠和一位瓦匠一人安放一边,同时还在横梁的两头各绑上一条糕,是专门给他们两位的。梁安好后,房屋便落成了。而一般老匠人把一生中获得的糕作为自己炫耀的资本,显示自己手艺的高超。
现在同时获得两条糕,这是多么大的荣誉呵!老外祖父这时还不到三十岁,正是年轻气盛的时候,受不住别人激将。可这件事实在是太危险了,在那上面作业,稍一失手便会掉下悬崖粉身碎骨。他冷静地思考着,然后向这项工程的主管说:我可以上去将瓦盖好,但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那就是必须用茅草将屋基的四面铺盖起来。茅草铺盖了屋基四面,就将人的视线挡住了,看不到下面的万丈绝壁,心里就安定了。他终于在众人的注视下盖好了屋顶。
我父母亲的婚姻是老外祖父决定的。那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父亲在乡里当通信员,在领导后面跑跑腿。1954年,二十一岁的父亲被领导分配到这个村里蹲点。在一次社员会上,父亲的演讲以及谦虚的举动博得了老外祖父的极大好感。其时,我外祖父正担任村长,父亲与外祖父一家接触多了起来,这桩婚姻便定下来了。
外祖父名叫左荣长,是个瓦匠,是跟随本家的一个长辈学徒的。他是外祖父的父亲唯一存活下来并成了家立了业的儿子。他没有正式读过书,小时只在私塾里上过一年学。外祖父十九岁的时候,即1940年,在师父的引导下,他秘密地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组织。那一年,他的第三个孩子(包括出生后不久即夭折的我母亲上面的一男孩,在农村,也应当算一孩子),即我的母亲出世了。
新中国成立后,新生政权需要大量的为党工作的干部。组织上决定派外祖父去学习,回来后为党工作。但外祖母整日整夜地哭着不让他走,外祖父便参加了基层政权建设,担任村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后,又担任大队长,直到1968年,“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发动后,在一片打倒当权派的口号声中,外祖父才愤然辞去了大队长的职务,又回家干起了自己的老本行——瓦匠。
外祖父个头较高,身材魁梧,永远穿着一件黑平布中山装,干手艺活时在腰间再围上一条黑围巾。他不苟言笑,表情很严肃,平整的头发向后梳起,稍有些谢顶的前额有几道浅浅的皱纹。
他很爱学习,劳动之余,总喜欢看看书,练练毛笔字,或抄些谚语、对联、节气之类的到笔记本上。每年过年时,整个村庄和生产队的门窗上的对联都是他一人写的。他的字写得很好,很老到,一般的高中毕业生的字是沾不上他的边的。
母亲是外祖父的第三个孩子,十七岁时嫁到父亲老家,在生下她的第一个孩子后,便到县纺织厂去上班。那正是“三年最困难的时期”,粮食短缺,工人比农民的日子更加难过(工人只靠国家发给的定购粮,农民毕竟还有一些自留地)。母亲此时正怀着第二个孩子,整日的劳动却吃不饱肚子,丈夫在乡下工作,相距很远,大孩子寄托在娘家,心里怎放心得下,母亲便决定辞职回家。但这时祖父已带着一家人逃荒到江南落户,老家已没有人。祖父在江南立足未稳,日子正艰难着,怎么办?最后还是外祖父接纳了她。
从此,我的家就根植在这个小山村里,这个四面环山的小山村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