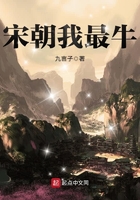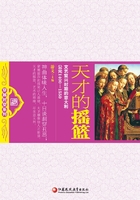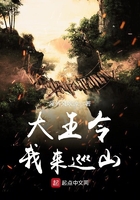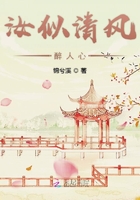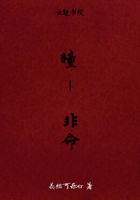“快避开!。”
突然,外边街道传来一声怒吼,接着便是一团团黑影从街上穿梭,走在前头的是骑着高大骏马的中年人,腰带秦剑,神采奕奕。
因那酒肆靠近东城门,所以行兵总要经过这地,附近的百姓也没大惊小怪(毕竟每个月总会有这么几次),只是让开道路,站在一旁,继续做着自己的事,只是有些青年时不时冒出异样的眼光看着那将领。
秦好战,以军功授爵,以致秦人闻战而喜,闻战而欢,不过除了一些特殊时期,也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参军的,毕竟还要有人务农,事生产,以保证这战争机器的供给稳定。
不过那可是军功爵啊,那是封田赐爵,那是一世荣华,那是普通百姓往上爬的唯一路径啊!
况且就算自己战死,它也能庇福延至家人的啊,怎能让这些青年不羡慕嫉妒呢?
“怎么,翦兄,识得那人?”望着王翦看着那将领的炙热的眼神,蒙武打趣道。
“不识得。”王翦说罢,捧起一坛酒,闷闷地喝着。
那将领他是不认识,可那军队他识得,那是咸阳卫军左军,看那架势,势必是增援邯郸战线,看来这一仗,秦王势在必得,可是一切都与他无关,他只是个市井酒徒罢了,只不过他似乎看那将领得意洋洋般的模样不顺眼罢了。
“嗯。”蒙武也不深究,别过头来陪着王翦喝起酒来。
军队如风过境,只带走一些尘埃,留下一片宁静。
······
咸阳城外,渭河旁。
一只小船挨靠岸边,船头上站着个蓑衣人,杵着木桨,望着岸上的抓着竹简的黑衣人。
黑衣人看着约摸四十岁左右,面容已有衰老之势,本就稀疏的鬓发夹着些许白发。
“大兄,真要如此么?”蓑衣人喊道,“那蜀地乃莽荒之地,且毒虫病多,恐怕你的身子······”
听闻,黑衣人轻笑一声,将手上的竹简收了起来,双手抱拳道:“爹娘就拜托了,记得,若有事,去咸阳寻那魏先生,他自会帮你的。”
“知道了,知道了,别老学爹娘那样。”蓑衣人摆了摆手,“那我回去了。”
说罢,蓑衣人放开系在木桩的绳子,撑起木桨。
“自个照顾好自己,到时病倒了可没人照顾你。”
黑衣人看着那小舟越来越远,直到化为一个黑点时,才把头别过,望着前面那座咸阳城,咧嘴一笑。
————————————
齐国。
“夫子,学生有一事不明。”
“额?”荀况望着因小跑而脸色涨红的李斯,放下手上的竹简,“何事,但说无妨。”
“秦以法治国,夫能御五国而霸诸侯,那么。”李斯长吸了一口气,“夫子以为,法治天下如何?”
儒家迂古,道家不争,墨家不为王权,这天下就只剩下法家了啊。
想着,李斯紧握着拳头。
“圣人曰:‘君为舟,民为水。’水可承舟,亦可以覆舟,法松则国不治,法严则民不服。”
“学生知道,可是······”
“况且李斯啊,不要忘了,现在这个天下,还是周天子的天下啊!”
周,以礼治天下,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这天下有哪国不是呢?又谈何法治呢?
“那么,学生请教夫子,何以治国?”
看着脸色有些倔的李斯,荀况笑了笑,似乎想起了早年自己到稷下学宫求学的那般模样,便提起了兴致,讲起了自己游说诸侯的那般说法。
“内以王道,外以霸道,术势辅之。”
说到底,荀况也还是儒家的人,就算学遍诸子百家,他的根到底还是儒家的,他最坚持的还是礼治天下,而法术势只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工具罢了,只是他的两个弟子似乎有点走偏了。
李斯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突然,他似乎想起了些什么,开口问道:“夫子啊,你游说诸侯时有没有发生什么趣事啊。”
“趣事啊?”
荀况想了想,似乎没有,毕竟大部分都是被人以礼相待,然后丢在一旁不管,让的自己自找没趣离开,不过好像还是有一件的。
“我见着了鬼谷传人。”
“那秦国的魏先生?”
望着李斯一脸‘那算什么稀奇事’的模样,荀况笑着说:“是另一个,我在楚国遇到的。”
“啊?”
“鬼谷双子,一代鬼谷必有两个弟子,这有什么稀奇的是吧?但两个鬼谷传人都效力于一国,你可曾听闻?”
两人共效一国,难道两人不是相拒的么?
如此想着,李斯老实的摇了摇头,表示前所未闻。
“更稀奇的是那鬼谷传人的志向,致学天下。”
“致学天下?学生不懂。”
“兵者学兵书,农者学农书,工者学工书,使天下皆有所学。”
李斯冷吸一口气,下意识道:“这不可能!”
莫说天下了,就连书以天下也是不可能的事,毕竟那时的书可不便宜。
“这自然不可能,不过这般作风倒也符合那群人,心里装的是这天下,不像我们这类人。”
说着,荀况笑了一下,似乎是在自嘲,“不像我们,以学闻天下,到头来却只是赚的个名声罢了。”
天下之地,竟没有地方容得下他那一身学识,他只得回到稷下学宫整理先贤的学说,或是立书载道,毕竟连这齐王也容不下他那天下学说。
也不聊了多久,天色已经暗了下来,王城的灯火已经亮了起来,满天的繁星不厌烦地闪着亮光。
“老师,学生就先告退了。”
李斯看着那点着烛火开始整理闪乱竹简的荀况,拜了拜拱礼,便起身离开。
荀况看着忽明忽暗的烛光,突然说了句:“若为法家,秦国为上,魏为中,赵为下。”
李斯顿了顿,笑道:“学生明白。”
然后,李斯便离开了,房间里面又恢复原本的冷清,只剩一个老人秉着蜡烛,收拾着桌上散落的竹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