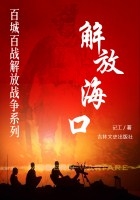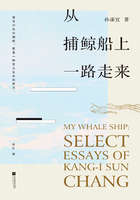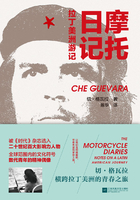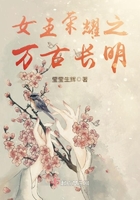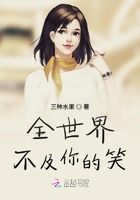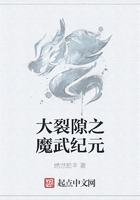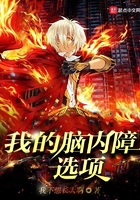杂文是什么?用鲁迅的话说,“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用瞿秋白的话说:“鲁迅的杂感其实是一种‘社会论文’——战斗的‘阜利通’(feuilleton)。谁要是想一想这将近二十年的情形,他就可以懂得这种文体发生的原因。急遽的剧烈的社会斗争,使作家不能够从容地把他的思想和情感熔铸到创作里去,表现在具体的形象和典型里;同时,残酷的强暴压力,又不容许作家的言论采取通常的形式。作家的幽默才能,就帮助他用艺术的形式来表现他的政治立场,他的深刻的对于社会的观察,他的热烈的对于民众斗争的同情。不但这样,这里反映着‘五四’以来中国的思想斗争的历史。杂感这种文体,将要因为鲁迅而变成文艺性论文的代名词。自然,这不能够代替创作,然而它的特点是更直接迅速地反映社会上的日常事变。”
那么,除了“更直接迅速地反映社会上的日常事变”之外,杂文还具有什么特点呢?只要拿杂文和一般社会科学论文比一比,它的特征就显露出来了。它常常活灵活现地描述事物、而不是抽象地说理或是平铺直叙地举举例。它又常常从字里行间露出作者的音容性格(这是那个作者倾注他的感情,亲切地谈话的缘故)。正是由于具备这些特点,杂文才成其为文学。
作为散文的一翼,杂文和其他文学形式一样,是“古已有之”的。“详夫汉来杂文,名号多品。或典、诰、誓、问,或贤、略、篇、章,或曲、操、弄、引,或吟、讽、谣、咏,总括其名,并归杂文之区”。宋玉始造《对问》,枚乘首制《七发》,扬雄肇为《连珠》,“凡此三者,文章之枝派,暇豫之末造也”。其后的“杂文”,以至“五四”以后周作人、林语堂们的小品文。也大多是文人学士的闲适之作,供人们观赏的“小摆设”。鲁迅先生认为:一味粉饰太平、玩世不恭的小品文,“常人厌之,阅不终篇”,是没有出息的。他“乐观于杂文的开展,日见其斑斓。第一是使中国的著作界热闹、活泼;第二是使不是东西之流缩头;第三是使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在相形之下,立刻显出不死不活相”。正是由于鲁迅先生把“古已有之”的小品文做了脱胎换骨的改造,才使之得以从小品文中脱颖而出,成为匕首、投枪一般的现代杂文,即鲁迅风杂文的。
当然,我们这个时代与鲁迅所处的时代已经大不相同。但是,难道我们这个时代,就不再需要匕首、投枪式的鲁迅风杂文了么?林帆同志在《杂文与杂文写作》一书里说得好:“解放以来,我们的文艺界就是以歌颂的作品占压倒优势,新闻界长期以来就是报喜不报忧!也许是这个缘故,后来蓬勃兴起一种歌颂性杂文,而且有人主张,杂文应该以歌颂为主。杂文以歌颂,又是为主,这好比要求川菜去辣加糖,失其四川味了。”
当然,不会有人反对运用杂文进行歌颂。歌颂得巧妙,未尝不是一种新品种。只是过于强调,或者怕招惹非议而以美代刺,恐怕会导致杂文写作的萧条,甚至会强扭了杂文的性格。李瑞环同志不久前指出:“开展批评,是我们党领导的事业及自身建设的需要,也是我们党有自信心、有力量的表现。……经常有一点严肃认真的批评,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态度鲜明,就显得有生气,有战斗性。群众的愿望、意见、要求得到了反映,心情就舒畅,积极性就高涨。群众的情绪能够通过正当渠道得到疏解,就不至于来个‘总爆发’,也有助于整个社会的稳定。”由此看来,匕首、投枪式的杂文仍将受到欢迎,是大有用武之地的。党和人民群众所以需要杂文、欢迎杂文,因为“蒸馏水般纯洁的社会”现在还没有实现。而且,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论断,那是永远也不可能实现的。
毋庸讳言,我推崇“鲁迅风杂文”,但也无意排斥“新基调”。秦牧同志说:歌颂性杂文未必一定是“媚骨”的产物,关键是看你歌颂什么,是否恰如其分,是否体现真理。“歌颂彭德怀正所以批判压制民主的现象,歌颂张志新正所以鞭挞当年倒行逆施的丑类。”这当然不无见地。同样的道理,批判压制民主的现象,鞭挞当年倒行逆施的丑类,亦正所以歌颂彭德怀、张志新。“是是非非谓之智,非是是非谓之愚。”讴歌真、善、美是对的,针砭假、恶、丑也是对的;反之,则是错的。问题不在于讴歌还是针砭,而在于讴歌的是不是应该讴歌的、针砭的是不是应该针砭的。不过,作为“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杂文似乎更宜于以“鲁迅风”为主旋律。因为,杂文若非“鲁迅风”,就没有锋芒,没有战斗性,没有杂文的特色。当然,“主旋律”之外,“大三和弦”“小三和弦”也是需要的。“相竞而兴,专占而萎败”嘛!我期待着足以与《马尾巴、蜘蛛、眼泪及其他》《谜语新闻好》《痛苦三章》《笑说“茅台”不是酒》等鲁迅风杂文媲美的歌颂性杂文问世。这无疑寄望于新基调杂文家们的努力。
也许是由于杂文“善恶必书”、锋芒毕露,时不时地总要“冒点酸水”,弄得某些人不太愉快,甚至刺得人家又痛又痒的缘故吧,它从来就是“生不逢辰”的。然而因为大多数读者欢迎,所以它又有无比的生命力,压而不垮,枯而复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时候都不是杂文的时代,任何时候又都是杂文的时代。唯其如此,杂文家们需要动脑筋、花力气进行研究的,就绝不是要不要写杂文的问题,而是如何写杂文,或曰如何增强杂文的逻辑力量,充实其“杂文味”,使之在宣传媒体的占次要地位的一角大放光彩。至于某些人对杂文及其作者说三道四,那也是“古已有之”的。这用得着但丁的一句名言:“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我深信,只要杂文界同仁坚持“‘二为’方向”(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双百’方针”,并且“乐观于杂文的开展”,就一定能够“日见其斑斓”!
(原载1991年4月10日《四川交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