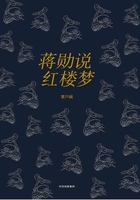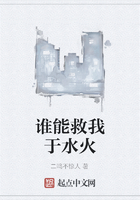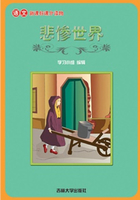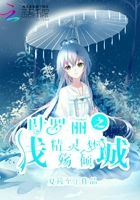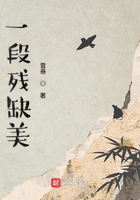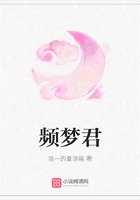几天下来给老爸发短信打电话带他出去吃饭,带他出去玩,带他逛这座我度过四年的城市。虽然有堆积如山的任务、放不下的学业,还是无心顾及。和老爸在一起的时候倒觉得他像个孩子,会耍小脾气。每次叮嘱他记得添衣,记得下飞机之后找机场大巴回家,老爸都拍着胸脯说:老爸走南闯北很多年,没问题!
老爸总是说自己没问题。记忆里老爸也确实没有和我提起过什么“问题”。
想想,自己很努力,也不为什么特别的好处,顶多也是让他为我骄傲,如此而已。
相逢何必匆匆——关于龟、诺贝尔和爱情
多少年过去,脑海里最美的画面,竟然是那天夕阳西下,我们一行人徒步走上斯坦福背后的山岗。夕阳很暖,山下的海湾和城市一览无余。落日将我们的剪影留在地上。我牵起离我最近的男孩的手。太美的景色已经难以用言语表达,更无法延迟到文字生成,我只想握住一只手。
某人指了指电脑屏幕上《中国古代房事考》的一行小字,一脸坏笑:你知道你为什么喜欢龟了吧?我瞥了一眼,感觉和当年放在我桌子上的《性经验史》一样,都是拿生活去做学问。做着做着就走丢了。
我喜欢龟,是因为龟的眼睛亮而无神,盯着我看的时候慵懒无力,像很多人眼下的境遇。
我经常喜欢妄下断言,然后用生活中不时涌现的细碎事实打破它们。比如我以为自己大概永远不会写昨天那样的文章。自恋狂。但是拿起笔还是一样。说来说去,马尔克斯的自恋与我的自恋究竟有什么差别?这种自恋让人读《霍乱时期的爱情》时深深一叹:原来爱情还可以是这样?!回过头,却听见耳边响起的嘈杂声:情侣间的甜言蜜语或是尖酸刻薄、保研还是直博相互纠缠、谁和谁……
那天我突然决意下辈子变成一只龟,不是因为寿命,而是因为它可以躲避、伸缩和冬眠。总之是对外物的可理可不理。
想永远这样同一种制度的东西疏离。不必争抢好处,争风吃醋。也不要暗自揣度、钩心斗角。这些统统都不擅长。最好就是开一家不必盈利也可生存的咖啡店,购来所有爱读的书,细心装潢,然后捡拾起似乎已经荒废多年的水笔、细细涂鸦。领养一只慵懒的猫,不要怕人也不要黏人,走路的样子像踩在皮球上的轻盈和悠闲。人说,猫都是得了抑郁症的孩子。每晚在宿舍楼下的夜影中和喵星人聊天的时候,它们的样子就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感觉,倒让人舒坦。
那天经历了种种不快。送快递的大叔一副猴急的样子,连连催促,理由是:我有心脏病。我的朋友冲下楼取到快递的时候,他只愤怒地说:我有心脏病。我突然想起了王小波,没有理由。读王小波,就像读一个疯子的呓语,疯疯癫癫、狂妄无比却真实得让人心悸。他不吝曝露自己不光鲜的肉身,给这个诡异的世界看。然后抖落他对生活和世界的只言片语,用诡辩的逻辑嘲笑自己的迟钝,却是在嘲笑底线崩塌的人世。
当天莫言捧得了诺贝尔奖的时候我正在咖啡店里读书。有人突然大叫了一声:中国人得诺贝尔奖了!周围的人纷纷议论起来,那骄傲的神色有如自家的闺女被外人看中了准备出嫁一样。可是他们却从来不曾了解过她出嫁的资质何在。显然那是无所谓的,只要嫁了出去就不愁有人再说闲话,怀疑全家人的能力、地位和水平,甚至扯上了什么族的关系。这回,通通没有关系了。全家人可以光明正大地骄傲一次了。
当晚,我梦见自己站在一个巨大的舞台上,也许真的是诺贝尔奖的颁奖台。梦里,那是一个舞台,和戏剧落幕后的冷清一样。翌日清晨,我笑着醒过来。隔了一日,我才想起自己笑的原因。大家在表演。隔了几日,在一堂文学课上,老师说,中国当代有哪个人算得上是真正的文坛巨匠?老师细数了北岛、王安忆和余华。接着老师说:王小波死了。我的心突然无限地沉下去。好像在说一个熟悉的朋友。或许是他的文字太奇异罢,只能在制度外围做英雄。因为在这个地方,一些东西真的经不起他这样的幽默与嘲讽,一些人宁愿自戳双目也不愿看着他明目张胆地“堕落”。我怕我们真的失去了太多单纯,以至于有一天醒过来不认识自己,不记得童年,还不屑于抱怨不公。
我问一个朋友,我怎么运气这么差?他想了想,戏谑道:你对待这个世界的方式太不严肃了。突然想起了去年的这个时候,自己大概还在英国错综复杂的街道上用男人一样的嘶哑嗓音唱歌。那个时候多少带着点儿因为愤怒和迷茫产生的莽撞,于是把全部的虚无缥缈的希望寄托在异国他乡的每一个过客身上,或者是能够让人产生幻觉的浓烈的酒精中。直到我遇到了那对基督徒夫妇。只要他们家中的烛光亮着,我就多一分坚定。他们为我熬的鸡汤,至今想来都让人禁不住热泪盈眶。男人说:我爱她,因为上帝知道我爱她,把她安排在我身旁。那女人算不上传统意义上的顺从和贤惠,可是却善解人意。我接过熬好的鸡汤同他们道别,之后就再没联系过。
去年今日。我大抵还在流浪——自诩的流浪,实际并不落魄。想起那夜一个人在凌晨时分到达英国北部的工业城市阿伯丁的时候,只听到船头长久的轰鸣。我以为自己可以在寂寥的时空中走着走着就死掉,然后心甘情愿地接受上天这一份美妙的馈赠:孤独的行走和安稳的死亡。一年间每当我深感孤独或落寞,就想起那夜持久的轰鸣声。那一刻,彻底地被遗忘并没有让人超然,反而徒增了惶恐。我就那样惶恐地走在异国一座又一座陌生城市的街头,深夜的寒霜笼罩在昏暗的路灯上,海鸟惊惧地起飞降落。寒冷让人绝望。
同样让我留恋的,还有斯特灵的落叶。寂寞的苏格兰。那里的威士忌酒、庄严的古堡、高低错落的荒原、风中尖利的风笛、冬季阴霾的天宇……一切的一切都成为日后梦中的布景。若干时日之后,当我无意间看见人任何关于它的信息,当我借着寝室不算明亮的灯光在夜里捧读《呼啸山庄》的时候,竟然觉得自己就站在一片辽阔的荒野上,四下无人。狂风呼啸,黄叶遍野。
还有哈佛大学门口的那条热闹的街道。唱诗班在小广场上站好,迎着晚霞歌唱。小孩子们四处奔跑,漂亮的姑娘和健康的小伙子在街角的咖啡店小声交谈、神秘地笑着。还有一位年轻的父亲领着自己年幼的女儿在街上散步。我时常觉得那首叫What a Wonderful World的歌写的就是这里。歌词里说:“我看到蓝色的天空,漫步着白色的云朵。仁慈的白昼与神圣的黑夜有序交替。当我置身其中,哦,世界多美妙!绚丽的彩虹横卧苍穹,七色的光芒映照着过往行人的微笑面容。我看到就别的老友们彼此握手,问好。正将‘我爱你’深情地告诉对方。世界多美妙!”
原来曾经的这些际遇都已经融入你的神经和血肉,除非死或是失忆,不然它们会一直与你同在。不论是呼啸山庄带给你的感受还是那些诗句引起的共鸣,都是你当初就已酝酿的云霞。
一直不相信那些照片中的岁月。好像快门按过之后,那一刻就永不复返。儿时因为不断躲闪,浪费了胶卷,被父亲责骂。有一日数码相机取代了那些原有的笨拙,技术革命大行其道的时候,突然想念起那日在公园中,父亲为我修理坏掉的车子。他站起身给我拍照,相机发出嘶嘶的声音——没有胶卷了——那张照片没有拍成,却永远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我第一次吻了父亲的脸颊。
依旧不相信留影过后的日子怎么过。那些转瞬即逝的流华和光影。那些一期一会的人和斗转星移飘忽不定的际遇。
之前从未想过自己要活过20岁。似乎当我在医院度过一部分童年的时候仿佛就已经顿悟生死,所以从不觉得健康长寿是怎样的祝福,虽然时时以此宽慰老人。当我读到约翰·克里斯朵夫说,20岁以后的日子不过是机械的重复,毫无新意的时候,才发觉自己已然走在这条路上。竟然安然自得。
那天在比较文学的课堂上,我讲完了自己的论文提纲,关于波德莱尔和北岛的诗歌。那位感性的女老师讲到波德莱尔的《恶之花》时愤怒地说,这个世界怎么配他活!我还没有这个老师这样愤世嫉俗,所以并没有为逝去的人和流传已久诗感到愤怒。只是觉得忧郁背后有太多的华丽没有成型,就已经湮没在众人的迷茫中了。
多少年过去,脑海里最美的画面,竟然是那天夕阳西下,我们一行人徒步走上斯坦福背后的山岗。夕阳很暖,山下的海湾和城市一览无余。落日将我们的剪影留在地上。我牵起离我最近的男孩的手。太美的景色已经难以用言语表达,更无法延迟到文字生成,我只想握住一只手。
或许真的是太不严肃了。我还依旧握着他的手。他的眼睛盯着我,慵懒而无力,像我爱的那只龟。
对不起,我不是个歌颂者
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对我而言。不是白色情人节,因为忘不掉两年前那朵枯萎的玫瑰,为我遗留下的残枝败叶。
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对我们而言。不是圆周率日,而是最适合朗诵辛波斯卡的日子。这个风烛残年的老婆子写:“我们的时代仍未安稳、健全到让脸孔显露平常的哀伤。”(《微笑》)当然,她在写她的时代。她还说:“王冠的寿命比头长。手输给了手套。右脚的鞋打败了右脚。”(《博物馆》)
——给今天
11岁,不是爱上鲁迅的年纪,却意外地迷恋上了他的东西。后来索性按照他的文风写了一系列的文章,一部分交给了老师应付例行的周记作业,一部分被母亲在无意间看见。前一部分让我的本子上多了几行鲜红的批语,诸如:你还太小不适合谈人性、不应该这么悲观、未来依旧美好者云云。后一部分让母亲因为我不期而至的早熟忧心忡忡,还特意安排了一次长谈,我想是借此来诊断我的心理是否出了什么问题。母亲的举动虽然如今看来完全可以理解,毕竟没有一位母亲希望自己的孩子从小就染上愤青的毛病,悲观厌世到读鲁迅的文章击掌称快转而写些批判文章。可是那些鲜红的批语却成为心中的死结,终不可解。对于人性灰暗成分的剖析于我看来不过等同于对显微镜下细胞结构的观察,了解继而熟知并不是什么值得诟病的事,更和年龄大小无关。若干年后,我写了篇不短的文章企图论证“中国人的尊严”问题,核心意涵同王小波的《个人尊严》一书相似,不过添加些个人见闻和逻辑层面的补正,发到网上之后却意外遭到尖锐的反击。其中一个留言让人记忆犹新:“你以为自己是谁?鲁迅吗?”后面紧跟着数不清的感叹号,渗透着让人心寒的责难。攻击文章的人大多是在校的大学生,他们并不讲道理也懒得举例论证,字眼中却透露着不耐烦和蔑视的情绪,甚至还带有让人不解的人身攻击。
最为可悲的不是一味的谩骂和不讲道理,而是在阅读之前就已经框定立场。在这样一个立场分明、是非混淆的地界里,逻辑是否缜密、文思是否顺畅、言辞是否得当已经构不成评判一篇文章思想价值的主要因素,全权由“立场”来代言。于是,我们看见一群群怀抱着立场的人站在河对岸大声呼喊、肆意责骂,却看不见一条船能够破浪前进,告诉你你的逻辑究竟哪里不对。整场论证就如同马戏团表演一样哗众取宠,充满奴性的味道。尤其当面对所谓的政治敏感话题的时候,这些人便会故意放大音量,甚至呼朋引伴、气势汹汹,冠之以各种罪名。其中,最普遍的罪名之一莫过于“不爱国”。我来告诉你我什么时候被警告过“不爱国”。我佩戴着“用烈士的鲜血染成的”红领巾站在国旗下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时候,老师说你的声音这么小,是立场不坚定、不够爱国的表现。我在电视机前为奥运会赛场上的美国选手向终点冲刺而鼓掌欢呼,以及当我在英国留学时没有显出任何“想家”迹象的时候,同学说我不够爱国。当我写了那篇颇受争议的文章想要探讨中国人和英国人在对待个人尊严和国家尊严时所呈现的不同表征时,一位亲戚几乎歇斯底里地朝我大喊:“有本事你就到国外去!一辈子不要回来!真是可悲!”我几乎被这句话吓到,惊愕错乱之余不免陷入沉甸甸的伤感之中。因为我从不曾因为害怕鱼刺的存在而放弃吃鱼,也没有因为西瓜籽多而不再吃瓜,更不会因为家里的下水道堵塞而选择搬家。鱼、西瓜和那个堵了下水道的房子都是我得以寄存自我的地方,我咒骂鱼刺也好、讨厌西瓜籽也罢,都不会构成我不再依赖它们的原因。这个道理,总还算说得通吧。
在大学的课堂上,一些无知无畏的与我一般大的同学站起来反驳老师的观点。他们不同意书上将事件的原因归咎于一时疏忽的看法。可是对学生提出的一切怀疑的惯常解释是:中国这么大,乱的了么?中国有自己的特色!似乎这个国家就是一颗体形硕大的苹果,结构复杂,不可揣摩。这只大苹果被虫蛀了,咬一口满嘴的苦涩,吃的人不免骂一句。可是苹果商贩却对骂一句的品尝者说:你瞧!这就是这种苹果的特色,因为它实在是太大了!一个蠕虫算得了什么?这种逻辑你永远无法反驳,因为苹果之大人尽皆知,而蠕虫的存在会被商贩用各式的商标遮掩,表皮之下的腐烂只有商贩自己知道。我们只能成了对着苹果啧啧称赞的“托”。没有人不想做个歌颂者,尤其当苹果艰难的生长和它并不算糟的品相让我们心生怜悯之时。只是我们不能就此成为一个永久的歌颂者。这无异于飘零在大地之上的看似光辉却是背叛的异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