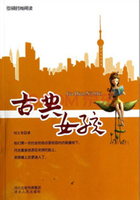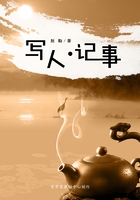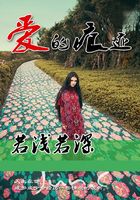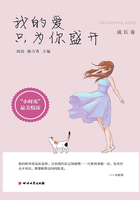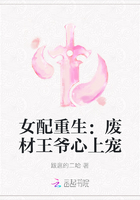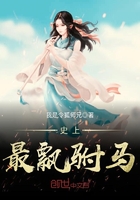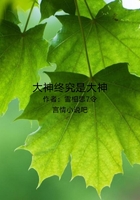于是崇尚中国古典诗歌的史蒂芬·欧文对北岛的《八月的梦游者》持怀疑态度,因为那些诗句“毫无中国特性”。[54]与此同时,洪子诚,作为从那个年代走来的知识青年,在《一首诗要从什么地方读起——北岛的诗》的讲座中对北岛诗不吝赞赏之辞。于是毛姆用以下这段话暗示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作为现实主义小说的成功之处,“小说家不可能提供一个生活的文学摹本,他只能为你勾画一幅他试图要显得逼真的画—假如他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如果你相信他,他就成功了”[55]的同时,纳博科夫则认为:“这部小说里充满了其他令人置信的细节…噎这样一部小说居然被称作所谓现实主义的里程碑,我不知道这现实主义的含义究竟是什么。”[56]于是当卡夫卡评论约翰内斯·贝歇尔的诗集时说,“诗句没有成为桥梁,而成了不可逾越的高墙。……语句在这里并没有凝聚成语言。那是叫喊,如此而已”[57]的时候,强调直觉、感觉和想象力的浪漫主义诗人们却用炽烈的诗句呐喊着生命,赞颂着自然。
作为局外人,我们不能单纯说孰优孰劣,孰是孰非,毕竟文学评论本身是没有对错之分的,只有好坏之别以及“有用”和“无用”的判断。我时常因此而觉得,作为一位作家和作为一位普通读者,看待文学本身的方式是不同的;作为一名文学评论家和作为一位普通读者,视角也是各异的。
在我真正写作之前,我只是站在那个世界之外看一出戏的观众,我觉得每个人都是对的,都是好的,都值得推敲,最多也只能算作品头论足。而当我拿起笔,写自己的东西,体会了一次萨特所说的在心中预设一位潜在的读者阅读的时候,才觉得我自己正站在舞台中央——这是一种奇妙的感觉,把自己当作写者而不是读者的角度会产生不同的心理共鸣。换句话说,我开始思考怎样做一名优秀的“演员”,演好自己的那出戏,而不仅仅是旁观者。所以当我读到卡夫卡认为这个世界有两种写作,一种是抒情诗一样的靠写事情在作者身上唤起的印象的个人文本,一种是写事件本身的艺术。前者是在“抚摸世界”,后者却是在“把握世界”。[58]中国文坛,抚摸世界的人太多,个体的情绪化的写作泛滥,却少有能够安静下来,用哲思和睿智把握世界的人。至于上述现象出现的原因,我想和中国传统中重感性轻理性,重集体轻个人,重秩序轻自由的特质有关,也和当下社会各种矛盾突显后世人的急躁不安的心理有关。事实上,那些在人类思想史中流传至今的作品,少有“抚摸”,更多是“把握”。
相似地,罗兰·巴特将作家区分为一般的作家和优秀的作家。前者是“及物”的,即作者由文字能够推想到现实世界;后者是“不及物”的,体现的文字和现实有一段鸿沟。于是产生了两种文学,前者是读者的文学,让读者无所事事;后者是作家的文学,赋予读者功能和角色。前者能够带给读者快乐;后者却足以破坏和质疑读者的一贯价值观而达到“震惊”的效果。
以上这段话给我带来极大的影响。曾经困惑于快餐式的小品文和经典的大部头之间的差距一定存在着远超过我自己所知范围的一些原因,可是却一直苦于找不到这种原因。我试图将其归结于作家自身的修养和性情,归结于不同时代读者接受能力和认知能力的差异,或者是大众价值观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变化。直到读到了上面这一段话,阅读了卡夫卡的那一段对于个人文本和文艺的差别的论述之后,才恍然大悟。
经历了种种反思的洗练之后,才渐渐发觉过度诠释的坏处。
于是下定决心:即便日后成为不了评论家,也要做一个能够独立思考的读者。
残忍的复仇与坚忍的等待——《呼啸山庄》与《霍乱时期的爱情》
当我读到他们在各自人生的航程中终于实现了最终的厮守时,眼前浮现出的,是一座脱离了市井气的城市,一条不那么澄澈的河流,一对已经熬过了大半辈子的老人,执手相看泪眼。
一部是19世纪英国女作家艾米利·勃朗特的《呼啸山庄》,以英国约克郡寒风怒号、枯叶卷席的无边荒野作为背景;一部是20世纪末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以南美哥伦比亚的小城喀他基纳炎热干燥、霍乱横行的泥泞河沼作为创作背景。几乎横跨一个世纪,贯穿地球两端的两段关于爱情与死亡的故事为读者展现出对于爱情感受的惊人相似。尽管各具特色、侧重不同,但小说里细腻的笔法、到位的描摹均伴随时间流逝而魅力无穷。本文通过对于两部小说情节(尤其是细节描写)、构架和其他等方面的比较分析,结合个人阅读体会,重点阐述两部小说中对于“爱情”与“死亡”这两方面的不同理解。企图借此寻找不同国度、不同时代、不同种族之间对于爱的把握和感受。
引子:荒野与河沼——爱情的发源地浅析
《呼啸山庄》中的故事发生在英国约克郡的荒原上,一个几乎与外世隔绝、冬季异常寒冷荒凉的枯叶荒原。笔者曾经在初冬一个晴好的天气里站在英国苏格兰地区的荒原上看着黑的白的羊群或站或卧,烈风从四面八方吹过来,四下无人的时候略显沧桑与凄凉。晴好的天气尚且如此,可以想见狂风或是阴雨这里将怎样悲壮。呼啸山庄就坐落在这样一片荒原上,故事的起初便充满着犬吠的凄厉、寒风的凛冽和空气中压抑、阴郁、扭曲的气息,让人读后顿生寒意与恐慌。在这样的环境中写爱情与死亡,就像在寂寞的宇宙间寻找依靠一样,在阵阵凉意中蕴含着凝重的绝望。似乎爱必须决绝才配得上这样的荒原。
有人将这部小说评价为“爱得这么深、恨得这么透的爱情和复仇小说”。爱就如同阳光笼罩的荒原一样,炽烈而焦灼;恨就仿佛狂风雨雪横扫的山庄一样,寂寞而绝望。不到30岁的艾米丽就这样抱着“无论生死,但求心灵无拘,又有勇气承受”的笃定愿望,写下了这让后世读之都背后发凉的残忍的爱情。和那凄厉的、孤单的大环境相互映衬,如虎添翼。在小说的开篇,山庄的女管家丁恩太太给受伤的洛克伍讲述山庄中发生的故事的时候说:“这一带的人比起城市里形形色色的人来,生活得更有价值,就像地窖里的蜘蛛比起茅屋里的蜘蛛那样……他们确实生活得更认真,更执着于自己,很少去管那些表面的变化,以及琐碎的外界事物。”接着,他说“在这儿,几乎有可能存在着终生信守不渝的爱情”。[59]诚然,城市中混杂的人群和紧凑的生活节奏大概只能生成俗世意义上的爱情,因为人们大多关注的是自我利益的实现和物质生活的满足。相比较而言,呼啸山庄的爱情中追求的是一种源自自然的天然情愫和诉求,当外界的枯燥已经耗尽生活中的乐趣的时候,人们便转向自我发现和自我救赎来丰满内心、践行爱情了。这一点在小说的主人公希思克利夫和凯瑟琳之间的天然之爱中得到最好的解答。后文将做进一步说明。
相比而言,《霍乱时期的爱情》的大背景就显得比较复杂,几乎可以概括成是喧闹、欢腾和冗长的结合体。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纷繁复杂、市井气息与魔幻氛围相交错、充满诱惑的南美小城喀他基纳可以说为整个爱情故事的发生、发展、成熟和死亡提供了最恰到好处的环境。在马尔克斯的小说中,他曾借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的视角描述这座小城的留下的最深印象。他称其为“穷人等死的墓穴”,在从西班牙统治中独立、废除奴隶制之后依旧带着“奴隶的印记”[60],至今仍处在“时代的边缘”。在马尔克斯的笔下,这座城市被描述为炎热干燥、夜晚充斥着令人恐怖的事、慢慢衰老的、众人在梅子丛中纵情狂欢的样子。它的复杂在于它既能让人感受到衰老的悄然将至,那种时间绵延和冗长以及过度欢愉造成的拖沓感;也可以让人从不同地区迥然不同的生活状态中感受到“青春期那种孤独的快乐”。[61]的确,在长期生活在大城市,经历千篇一律、循规蹈矩的生活的人看来,这样的殖民城市的独特韵味确实似一场梦、记忆中的幻觉、一段只能聆听不敢想象的遥远故事。
在这样的环境中,霍乱时期的爱情带给读者的味道少了一点佶屈聱牙或是冷酷无情,反而更增了其间的戏剧意味和传奇色彩。因为缓慢的生活节奏,男主人公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和女主人公费尔明娜·达萨才得以在相对长的时间里彼此揣度、享受神秘而纠结的爱情。也因为纷繁复杂、不断变化的生活环境,两个人才阴差阳错地走上了不同的生活轨迹,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幻灭了年轻时的爱情理想。然而需要说明的是,这样的幻灭总是以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一方心理的进退为转折辗转曲折,而费尔明娜·达萨的情感投入却更多地带有好奇、依赖和猜测的成分在。不同于《呼啸山庄》中凯瑟琳纠缠至死的依恋和决绝,费尔明娜·达萨的情感来得并不疾凑和陡然,好像她并未真正面对自己的内心呼唤。这一点在后文将会做进一步说明。
超越爱情——从两部小说男女主人公的相恋谈起
《呼啸山庄》中希思克利夫与凯瑟琳的爱情虽然并没有得到完全的发展,书中似乎也没有太多直接的描写,却一直以其绝望中浸透着残忍的意味、与死亡紧密相连的特点被后世铭记和慨叹。希思克利夫极端的恨和复仇情绪一直纠缠着他的生活,一直到死。有时我会怀疑这样的爱情在现实中存活的可能性。因为如果人天然有着向挫折和苦难屈服得以保全自我的本能的话,究竟是什么造就了希思克利夫不屈不挠地进行复仇?毋庸置疑,这当然和他的身世、性格和生长环境有关。希思克利夫,一个被山庄主人收养的孤儿,黝黑倔强不讨人喜欢,却在骨子里贮存了无比多的因爱而起的仇恨和丑恶的行径;而凯瑟琳,山庄主人的女儿,享受着富裕的生活,并没有遭遇过除希思克利夫之外的“挫折”。两个人之间的感情似乎并没有太多的铺垫,就似在无意中形成的一样。这种爱类似原始的爱的原型。按照柏拉图的说法:“爱根植于人类的古老由此可见一斑,它带领我们重返原始状态。努力合二为一,愈合人的裂痕。每个人都只是整体的一半,而且总是追寻着自己的另一半。”《呼啸山庄》对于希思克利夫和凯瑟琳之间的爱情的表现同这种说法有着惊人的契合,只不过从凯瑟琳的角度来看,爱情似乎连“裂痕”都不存在,而是同自身灵魂的完全的统一。
凯瑟琳这样描述她同希思克利夫的爱:“我这么爱他,并不是因为他长得英俊,而是因为他比我自己更像我自己。不管我们的灵魂是什么做的,他的和我的是完全一样的”。[62]凯瑟琳的这种爱并没有因为自己身份的高贵和对方身份的差距而改变,也没有因为嫁给埃德加生儿育女而改变,甚至到死后都变成魂魄来所求居所。很多人指责她的物质至上和爱慕虚荣,而在我看来,她的选择本身也是一种爱。正如她自己说的那样:“要是希思克利夫跟我结了婚,那我们还不是要去讨饭了吗?而要是我嫁给林敦,我就可以帮助希思克利夫站起来,安排他摆脱我哥哥的逼迫和欺压。”[63]向往自由、性格倔强刚强的凯瑟琳,渴望让希思克利夫也获得他该享有的自由,因此而选择“背叛”。这样的选择并不代表放弃,因为这两个人之间的爱并没有一丝一毫放弃的可能。从凯瑟琳这边看,她说“对林敦的爱,就像林中的树叶。当冬天使树木发生变化时,时光也会使叶子发生变化。而我对希思克利夫的爱,恰似脚下恒久不变的岩石,它虽然给你的欢乐看起来很少,可是必不可少。”[64]凯瑟琳并没有因为追求短暂的快乐或是物质而放弃爱希思克利夫,也不能单纯理解为她是因为爱慕虚荣才选择了埃德加。因为她的心思是笃定的。
从希思克利夫这边看,他的爱因为复仇而愈发狂热,也因为狂热而丧失理智。他因此而自暴自弃。在得知凯瑟琳嫁给埃德加之后,他说:“两个词就可以概括我的未来了:死亡和地狱。失去了她,活着也在地狱里。”[65]因为爱,他产生了邪恶的报复念头,并很快付诸实践。他通过赌博夺走了亨德雷的家产,又让亨德雷的儿子哈里顿成为奴仆,娶了埃德加的妹妹伊莎贝拉进行迫害,还让埃德加的女儿小凯瑟琳嫁给自己即将死去的儿子小林敦。最终将埃德加的财产据为己有。这样的复仇并没有给希思克利夫带来多少成就感,相反却让他“耗尽一生”,“在期望它的实现中被吞没了”。[66]他的成就感和幸福感来自于临死前耗尽心神而带来的幻觉,以为他可以和凯瑟琳在一起了。他在失踪了一晚后兴高采烈地回来,兴奋地说自己“看到我的天堂了”。[67]
在我们为这样执着、绝望而凄惨的爱情而唏嘘时,反观《霍乱时期的爱情》中男女主人公之间的爱情,则显得更加温柔和绵长,却也浸润着类似的情绪,即因为对方的喜乐悲忧而牵动神经,因为苦于思念而自我折磨,因为得不到而产生报复心理。在这些方面,两部小说在处理爱情细节方面的手法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