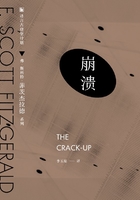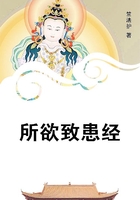和希思克利夫的出现类似,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也是以相对孱弱、无助的形象出现的。年轻的弗洛伦蒂诺在花园里战战兢兢地等候自己心目中默默仰望的女神的出现,制造各种机会和她见面却不敢开口表达。这个“孤独的狩猎者的秘密生涯”在愈发强烈的感情中爆发。在经受了相思之苦,甚至“迫切地希望自己死掉”而却依旧甘愿“享受煎熬”④之后,终于付诸行动。他的行动浪漫而富于憧憬的意味,比如雇一个小男孩帮忙打捞18世纪的西班牙沉船,得到船上的财宝从而能让费尔明娜过上好日子的天真幻想;比如作为唱诗班的乐师参加葬礼,让费尔明娜感觉到“其他乐器都是在为众人演奏,只有小提琴是为她一个人拉的”[68];比如连日不吃不喝不睡拼命给费尔明娜写信;比如夜晚站在窗外为费尔明娜演奏小提琴小夜曲,甚至因此而险些被捕;他在信件中夹上山茶花和头发向费尔明娜求婚;甚至在洛伦索·达萨威胁他让他远离费尔明娜的时候义正言辞:“如果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我无法给您任何回答。否则,那就是背叛。”[69]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始终抱着对费尔明娜的忠诚,甚至为她而保留自己的童贞。他的诗人一般的气质为他所做的这些事情下了一个恰当的注脚。他自称自己除了爱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要。唯一的遗憾也是没能为爱而死。
而在费尔明娜看来,旅行前对弗洛伦蒂诺的爱更多是出于对他造成的神秘感的好奇心,虽然最终逐渐转变为渴望和期待,也没能逃脱因为旅行艰难和时间空缺带给她反省自我的机会之后的放弃。这一点同《呼啸山庄》中希思克利夫和凯瑟琳的隔阂有着惊人的相似。后两个人在一个雨夜误闯画眉山庄被捉,凯瑟琳作为“小姐”留在山庄养伤,而希思克利夫则被逐出山庄。两个人开始出现隔阂,因为五周之后,当凯瑟琳返回呼啸山庄时,已经是一位“娇艳优雅的闺秀”,并因此而受到画眉山庄的林敦少爷的追求。希思克利夫原本就自卑的性格因为这样的转变而蒙上了一层阴影。
相似地,在《霍乱时期的爱情》中,费尔明娜在父亲的逼迫下开始了一场惊心动魄、记忆深刻的旅行。在这场旅行中,虽然没有和弗洛伦蒂诺断绝来往,但是由于身边风景和风土人情的变换、姐姐伊尔德布兰达·桑切斯的陪伴和照顾,她“重新认识了自己,第一次感觉到成为自己的主人,感觉到被陪伴和被保护,胸中充满自由的气息,这让她恢复了宁静,又有了活下去的愿望”。[70]回家之后,她“已经不再是那个既受父亲宠爱又受他严加管束的独生女了,而变成了这个满是尘土和蛛网的王国的真正的女主人”。[71]这样的转变对于费尔明娜而言是可贵的,在于她终于逃脱了家庭和压抑的环境给他的桎梏和枷锁,让她能够操纵自己的命运,不再逆来顺受。然而也正是这样的转变,让她认清了自己对弗洛伦蒂诺的感情并没有之前所想的那样炽烈和投入。相反,当她再次见到他时,她发觉他们之间不过是一场幻觉。[72]或许是弗洛伦蒂诺的性格太容易给人造成仿佛在书中恋爱一般的假象,或许是他的方式从世俗的角度看太含蓄太没有进展,或许是他们之间机缘尚浅,总之两人因此而没有再见。爱情却并未因此搁浅。
关于《霍乱时期的爱情》中对于弗洛伦蒂诺的复仇情绪,虽然展现得不如《呼啸山庄》中那样淋漓尽致,却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首先是他对她的思念,在失恋的痛苦里,“他挨着那些最难熬的分分秒秒,时而化身为一位腼腆的王子或爱情的卫士,时而又回到他那伤痕累累的皮囊,变回一个被遗忘的恋人”。[73]他因此而打算永远不离开这座城市,因为是费尔明娜·达萨的城市。但是当他选择坐上邮局小艇的时候,他却分明“再没有闻到海湾的臭气,只闻到弥漫在城市中的费尔明娜·达萨特有的气息。一切都散发着她的味道。”[74]与此相似,《呼啸山庄》中的希思克利夫在得知哈里顿和凯瑟琳相爱后,并未阻止,而是想起了自己的女神凯瑟琳,他发现哈里顿身上有她的影子:“还有什么不跟她联系在一起的呢?还有什么不使我想起她呢?我哪怕低头看一下这地面,她的面容就印在地面的石板上!在每一朵云里,在每一棵树上——充满在夜晚的空中。白天,在每一件东西上都能看到她,我完全被她的形象所包围!最普通的男人和女人的脸——就是连我自己的脸——都像她,都在嘲笑我。”最后他意味深长地说:“这整个世界就是一部可怕的纪念集,处处提醒我她确实存在过,可我失去了她!”[75]因为爱情,爱的那个人永远存在在自己生活的每个角落,不因为时空的改变而改变。
再说复仇。弗洛伦蒂诺对于费尔明娜的爱也掺杂着复仇的成分,只是不如希思克利夫的来的那么决绝和残忍罢了。在得知费尔明娜即将举行隆重的婚礼时,弗洛伦蒂诺祈求上帝,希望在她即将为爱情宣誓的时候,“让公正的闪电从天而降,劈在她身上”,因为“这位新娘,只能是他的新娘,否则就谁的也不是”。[76]他甚至因为复仇情绪的感染而产生了费尔明娜依旧在苦恋他的幻想。除了对费尔明娜本身的对抗之外,他还希望乌尔比诺医生死掉。在一次同医生的对话中,他发觉医生仍有富裕的时间仰慕自己妻子,并和自己的程度不相上下。书中写道:“在27年无休止的等待中,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头一次无法承受这种内心的刺痛:眼前这个令人钦佩的男人必须死掉,只有这样他才能幸福。”[77]这种想法并不是一闪而过,在他同萨拉·诺列加决裂之后,加重了对她的思念,“他迫切地意识到胡维纳尔·乌尔比诺一声必须死掉”。[78]然而,由于自身的懦弱性格和保守的想法,弗洛伦蒂诺不可能将复仇付诸行动,更不可能像希思克利夫那样用残忍的方法对付自己爱的人。因此,他将关注点转向了时间。
特别是暮年到来之后,弗洛伦蒂诺感到“暮年的岁月不是奔涌向前的激流,而是一个无底的地下水池,记忆从这里慢慢流走。他的智慧渐渐枯竭”。[79]他感觉到时间的紧迫,怕自己挨不过死亡的威胁,因此加快了步伐争取费尔明娜的爱情。正如费尔明娜说的那样,他们之前没有继续是因为太年轻;而现在却因为太老。在两个端点处,爱情来得总是不那么时机恰好。好在两个人都守住了时间,在疯狂的旅行中,他们“仿佛一举越过了漫长艰辛的夫妻生活,义无反顾地直达爱情的核心。他们像一对经历了生活磨炼的老夫老妻,在宁静中超越了激情的陷阱,超越了幻想的无情嘲弄和醒悟的海市蜃楼:超越了爱情”。[80]
尾声:爱情、时间与死亡
纵观两部作品——《呼啸山庄》和《霍乱时期的爱情》——两对主人公的爱情的停顿一个因为死亡,一个因为时间。然而,希思克利夫对于凯瑟琳的爱情并没有因为凯瑟琳甚至是自己的死去而停止,灵魂的结合让读者坚信他们在死后还会相逢;弗洛伦蒂诺对于费尔明娜的爱也没有因为两人的老去而放弃,他们最终乘上了“新忠诚号”扬帆起航,在马格达莱纳河上来来回回,在年逾古稀的岁月里体会迟来的爱情。
一个是一辈子,一个是五十三年七个月零一天。在而今快餐式的爱情模式下,似乎很难想象这样持久的坚持。有人挖苦憎恨希思克利夫的残忍手段,有人鄙视弗洛伦蒂诺的懦弱和胆怯。可是毋庸置疑的是,在漫长的岁月考量下,两个人都经受住了考验,没有因为失去而放弃,也没有因为分别而背叛。一切似乎来得太过艰难苦涩,而少了点爱情的柔媚浪漫的一面。
当我读到他们在各自人生的航程中终于实现了最终的厮守时,眼前浮现出的,是一座脱离了市井气的城市,一条不那么澄澈的河流,一对已经熬过了大半辈子的老人,执手相看泪眼。
最初的与最后的高贵——读瓦茨拉夫·哈维尔《政治与良心》
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活动,无论是生态还是自然行为,我们都在试图做一件事情,就是企图将人类不断引向带有人文关怀的理性世界中去,以谦卑平和的态度对待自然,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狂妄的价值观,摆脱政治话语体系和宣传工具的错误导引,最终走向一个光明的、原初的、本来的世界中去。
卡夫卡说:“奇迹与暴力只是无信仰的两极。人们消极地期待出现指路福音,为此耗尽了他的精力,而福音永远不会到来,因为恰恰由于期待太高,我们把福音拒之门外;或者人们急不可耐地抛弃一切期待,在罪恶的杀戮中度过他的一生。两者都是错误的。”(《谈话录》)这句话应验于哈维尔在《政治与良心》中对于捷克共和国被迫选择苏联体制的来由的言论中的那句,“赤化总比死好”。哈维尔说:“这口号毫无疑问地表明说这番话的人已经放弃了他的人性。因为他已经放弃了某种能力,放弃了以个人的方式承担某种超越他本人之上的东西,甚至为这种给生命提供意义的东西献出自己生命。”
由于对至高的“指路福音”的迫切期待,人们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就是选择一个可以帮助他们自身脱离人性的指责,并且最大限度上逃避自身责任的方式。在舆论导向的指引下,在口号式、规模化的言论渲染中,人们一次又一次丧失了理智思考的能力,不自知地选择踏入理性的荒芜地和人性最灰暗的道德泥潭。有人把这种行为命名为“平庸的恶”(the banality of evil)。这种人类因为思想空白或者懒于思考而造就的灾难远胜于人类由于刻意作恶的本能而引发的灾难的总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人类一次又一次制造着这种“恶”。然而倘若推论到这一动因的根源,最可怕的莫过于,人们为了抵制这样的恶自制另一种权力和制度,最终走向另一个暴力的非人性的极端。其间起关键性作用的是言语的美化和目的的诗意表达。正是哈维尔所讲的“以更为诗意的手段征服人类良心”。语言美化后的政治概念和意识形态其实带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对于社会的精英阶层的误导效果和对于社会普通大众的感召力别无二致。就如同卡夫卡说得那样:“它们(指宣传捷克斯洛伐克大规模游行的政治传单)接收对象都是不现实的……它们的生命存在于说话中,存在于人的内部世界,而不在人的外部世界。”(《谈话录》)当一个经过政治包装的话语呈现在社会大众面前的时候,由于模糊的话语模式,普通大众的教育水平和认知能力有限,在缺乏判断力和独立思考能力的前提下,最有可能的情况是,他们自愿地将自身列入这个政治决定的受益者中,然后享受革命的激情和短暂的欢乐。政治,如果不是为了关怀人本身而存在的话,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话语的衍生。
韩少功在《暗示》一书中提到:“民主的谣言就不算谣言而只是说错了的真理,正像民主的暴力就不算暴力而只是做过了头的德行——民主所反对的专制,也标举过这同样的逻辑。”[81]当个人的主体意识丧失在科学至上、意识形态至上、政治万能之类的话语体系中,屈从于“客观”的论断和历史假设里,特别是无意识地降服于强大的权力话语中的时候,按照哈维尔的观点,我们把自己的责任转变成数字、科学、政治体制、理论本身的责任,从而期冀逃避人——作为理性选择的动物最应当承担的责任和后果——的责任。归根结底,是人性的弱点和人类中心主义达到极端的反射。尤其是,在现实的、立竿见影的、功利性的作用驱使下,人类的目光不得不转向切身利益、眼前的收获和短暂的欢愉。人们一次又一次放弃对长远目标的追求,也许不是因为没有预见到这些目标的正确性,而是由于人类的“理性选择”本身就帮助我们排除了这个选项。因此人类一代一代地走向对现实的利益的追逐,而自动放弃更高远更符合全体人类长期利益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
那么如何解决政治话语至上、非人性化统治的极权主义对人类的危害?答案是,不能直接将和这种制度有关的一切的一切都消除,包括意识形态。不能用极端的手段消除它,只能通过知识和智慧的开化、民主意识的觉醒来化解。如果站在人类历史的悬崖边上审视人类在面对极权主义、物质至上时的价值观选择,尤其是欧洲社会在现代化浪潮袭来的时候呈现出的自我怀疑、价值迷失的诸多现象,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其中惊人的共通之处——人类远离“本来的世界”之后的窘迫与无可奈何。
由于人类自身的活动的主观性和人类活动对自身的改造作用,“本来的世界”已经突破原有的概念,变为人类意志作用的结果。其结果是消减甚至消除了人对于天地和神明的自然依附和推崇敬畏心理,而变为着眼于人与人之间的实际关系的操纵、希望通过科学的手段改造世界的企图。我这里想提出的问题是,科学,是不是将祖先原有的对时空和万物的想象抹杀,去除了人对神的崇拜,而促使人成为世界秩序的规定者和掌控者?科学的至尊地位,是否象征着神性世界的泯灭和人性世界的为所欲为?人的道德底线和情操标准的答案是否能够仅仅在科学的领域里得到解答?科学,原本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的凭证、开发周遭的手段的功能是否最终逆转成其自身对于人性的质问?人类在自造的结果面前是不是能够恢复从前的天真和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