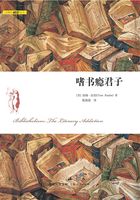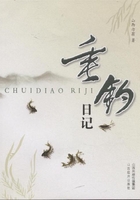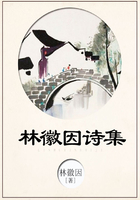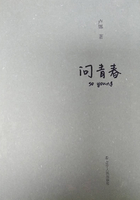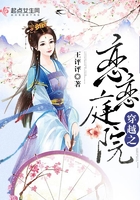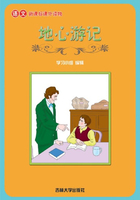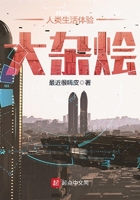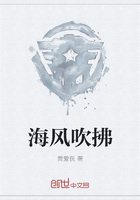哈维尔说,“我们必须受我们自身理性的引导,在任何条件下将为真理服务作为我们自己的基本经验”。问题是,我们“自身理性”能够引导我们走多远?甚至,理性引导行为是否有确凿的理论依据?“为真理服务”,是谁的“真理”?是否存在一种普世价值能够帮助我们衡量一切是非善恶?抑或是,真理本身就是变体,就是依照主体行为和观点不断变化的结果?
如果事实真如同卡夫卡所描述的那样,“上帝,生活,真理——这些只是同一件事实的不同名字。”“它存在于我们自己身上。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无法获得它的全貌。我们真正能理解的是神秘,是黑暗。……因为人无法突入上帝,他就攻击包围着神性的黑暗。他把大火扔进寒冷的黑夜,但黑夜像橡皮那样富有弹性。它后退,但它继续延续下去。消逝的只是人类精神的黑暗——水滴的光和影”。[82]
在这段表达中,卡夫卡默认了上帝的权威和至高无上的地位,同时也肯定了上帝、生活、真理的同质性——神秘和无法理解。由于神秘,我们无法把持它们的全貌,只能面对神秘自身。由于不可解,人只能世代传递思想,而无法用思想解决(原文用的是“攻击”)现实中的黑暗。于是我们在世代相传思想的过程中,只解决了自身精神的问题,即我们精神的黑暗(并非水滴自身,而只是它的光和影而已),并没有对上帝、生活、真理本身进行解答,这是人类一直以来面临的认知困境和智慧盲点。问题是,如果不走向“本来的世界”或是“生活的世界”,这种困境的出路和盲点的扫除是否有更现实更可靠的路径?
进一步的问题是,“本来的世界”是否可以通过理论上的返璞归真和心智的简单透明化达到?
哈维尔提出,“现代国家和现代政治权力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这里,一旦人类理性从人类个体、他的个人经验、个人责任感中分离出来,他也就背弃了‘本来的世界’的框架,背弃了与之相联的具体的责任感,背弃了他的绝对地平线。”那么,既然是人类理性与个人经验、个体意识的抽离的缘故,是不是有一种渠道是,通过恢复人类个体、经验、责任感在理性行为和思考中的地位和价值来恢复“本来的世界”的价值,从而建立全新的话语体系,根除极权政治呢?
英国现代主义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提出了她对于这个问题在文学上的解答。她试图突破文学评论家的身份,视自己为“普通读者”来阅读和评论他人的文学作品。在体会做普通读者的快感的同时找到一种能够帮助她脱离高贵的文学理论,转而关注文学本身的方式。她甚至引用约翰逊博士在《格雷传》中的那句:“一切诗人的荣誉最终要由未受文学偏见腐蚀的读者的常识来决定。”[83]
伍尔夫的观点,沾有“反智主义”的墨水,但是书写起来,却足以显示出她的智慧本身的单纯度。相比较而言,我们这个世界有时有着极其奇异的评价标准和行为逻辑。比如,我们原本是产生于这个世界之中的,可是在人类文明的历程中我们又不断被教会和这个世界保持距离。“人的成熟就是接受社会规范的过程,就是学会所谓分寸感即对周围很多事物保持距离的过程——这正是文明教育的目的。”[84]葡萄牙作家佩索阿说:“永远不要靠得太近——这就是高贵。”(《惶然录》)可是,当我们打着文明的旗号,或者说跟随着文明的波涛逐流的时候,我们真正远离的,究竟是“高贵”的对立面——平庸和卑贱,还是远离了高贵本身?我们定义的“高贵”,是不是很大程度上源自于人类中心主义的不屑一顾?
我们真的在“远离”的过程中高贵了吗?或者,我们从来没有拥有过高贵?抑或是,高贵仅仅存在于一定的话语体系之中?
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活动,无论是生态还是自然行为,我们都在试图做一件事情,就是企图将人类不断引向带有人文关怀的理性世界中去,以谦卑平和的态度对待自然,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狂妄的价值观,摆脱政治话语体系和宣传工具的错误导引,最终走向一个光明的、原初的、本来的世界中去。
语言是如何“乱世”的?——读韩少功《暗示》有感
在我合上最后的书页的时候,却看见一个眉宇间写满忧郁无奈的老农民,站在小乡村泥泞的田埂上,赤脚踏着泥土。背后是袅袅炊烟,手中的烟斗沉积着老烟叶。
韩少功先生在其《暗示》一书的开篇写道:“《淮南子》记载:‘仓颉作书,天雨粟,夜鬼哭。’有前人说,天降粟雨是对人间出现文字的庆祝。其实我觉得那更是一种警告,一种悲悯,一种援救,暗示着文字这种不详之物将带来乱世,遍地饥荒为期不远。”[85]
初读《暗示》,暗觉似乎篇篇都围绕一个主题展开,可是这“主题”却模糊如水中倒影,在朦胧的月色中辨不分明。于是再读,发现每篇都似乎在阐述文字和语言,但也有若干篇只是在讲故事,讲历史,讲自己,遂以为是在讲言语之内与言语之外的关联。心有揣测。于是再读,才发觉那句“一种警告,一种悲悯,一种援救”对于韩少功先生这整本书而言,就是微言大义,是千千万万个细碎意象的最终集成,是全书的精华如寒冷冬日之暖阳耀眼,是在期冀通过这些故事和片段阐释一件事情——“语言是如何‘乱世’的”。
本文从韩少功先生的《暗示》一书的文本出发,以个人阅读后的感受和与其相关的联想为主,想要通过个人有限的知识和一颗探求之心解决一件事:语言是如何“乱世”的?在我们经受着文明时代的洗礼的同时,是否还在不经意间承受着超越于蛮荒时代的人性危机?在我们得意于人类文明高度繁荣,科学技术统治生活的发展成果的时候,是否正在迎来下一个值得我们思索和省察的信仰危机?
第一,语言的出现和文明的进化让我们逐渐抛弃了沉默的习惯,逐渐忽略了言语之外的“意”。用韩少功先生的话说,就是“知识是基础性的危机之一,战争、贫穷、冷漠、仇恨、极权等等都只是这个危机外显的症状”。[86]福柯曾说:“我们的文化很不幸地抛弃了许多东西,沉默即其中之一。”[87]在报刊杂志电视网络等大众传媒充斥了我们的生活之后,我们渐渐习惯于接受他人的言论,并自觉地预设它们的正确性。当你走在街上,悬挂着各色标语的牌匾充满你的视野,公交车站的广告甚至覆盖了车次信息本身,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语言的交流,各大餐厅更是喧闹无比。当我们阅读着别人的观点,听着别人的音乐,每日里做无谓的日常交流,有多少话语是我们必须开口的?有多少文字是我们必须阅读和接受的?当我站在博物馆中,以一个文明社会的人的身份审视那些原始时代和文明社会初期制造的艺术品时,我不得不承认,那是一个绚烂至极的时代,是一个不需要太多语言和文字来表达思想或是承受文明的野蛮的时代。在被称为“文明社会的上升期”的现阶段,有多少这样精美、汇集人类发自灵魂深处思考的灵感的艺术品可以被制作?在商业符号覆盖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的时候,还有多少人,能够静静地坐在一件物品前面,将自己全部的心思和灵感都恰到好处地投射到上面,不为了利益的追逐和荣耀的收获,甚至什么都不为?
在《仪式》一文中提到:“仪式就是一种造像活动,就是人们不满足于交流之时,用具象符号来申明意义或者从中解读意义。”[88]他将那些铜器、石器、银器的精美归结于“精神感染”和“意志陶冶”。从这个角度说,我们日渐满足于日常交流,甚至沉醉于没有实际意义的交际活动中,当语言本身超越了意义而存在,语言不免成为空洞无神的符号。在这些零乱的符号的填塞中,我们认识生存的世界,对待自己的生活,遗忘着原初的宝贵的精神。那个重视精神感染力量,关注意识陶冶的时代似乎早已过去。正如《默契》一文提到的那样,“交谈是人际交往中重要的手段,却是生硬的手段,次等的手段,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最成熟的关系其实不需要语言”。[89]问题是,人在外界的渲染中逐渐走向聒噪和不安。那一段造门不前而返的“雪夜访戴”的佳话也在一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的余音中消弭无迹。[90]
也许真如狄更斯说得那样,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子女对父母再少有心头默默不语的惦念,而化作手机屏幕上的一条短信、电话一端的一声晚安。约会时的情侣之间再少有相对无言、含情脉脉的对视,多了些电影院歌舞厅的放纵。朋友之间再少有“君子之交其淡如水”的淡然牢固,多了些喝酒吃肉言语交情的累赘。
第二,人类对于文字本身的迷信和青睐造成了对历史真实性细节的忽略。《证据》一文中说得明白:“白纸黑字可以在历史中留存久远,而历史中同样真实的表情、动作、场景、氛围等等,却消逝无痕难为后人所知,而这一切常常更强烈和更全面地表现了特定的具体语境,给白纸黑字注解出了更丰富和更真实的意义。”[91]这进一步证明了历史研究的困难和挑战,当我们面对的是印在书页上的历史的时候,是不可以反馈信息只能够单向度阅读的时候,其实我们在默默接受着书中的“知识霸权”。这种接受往往不为人察觉,因而常常心甘情愿。所以当孟子提出“尽信书不如无书”的观点之后,知识分子们更加希望用这句话的提醒逃离书籍特设的语境,形成自己的独立判断。
陈寅恪先生在1929年所作的王静安先生的纪念碑铭中提到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也成为我们冲破思维框架和价值判断的牢笼的主要信念。这种思维框架和价值判断的牢笼是我个人的表述,用韩少功先生的话说,是“文字的独断”。[92]我们的历史,惯于“用公共化的文字来修建记忆,让不顺嘴的某些个人故事彻底湮灭,以求得思想安全”[93],而在此期间,我们忽略了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在对待过去的人为的灾难时趋于简单地定位,潦草地结案,甚至堂而皇之地搪塞大众,麻痹公众的视听。可是,我们终于要面对的,不是历史本身么?不是曾经由我们的祖先的血脉沿袭下来的传统,所犯的过错或是所创造的成就吗?《忏悔》一文的末尾总结得精妙:“一种新的思想专制和新的思想极权正在悄悄形成,并且在‘政治正确’的名义下积重难返。”[94]
文字塑造事实。事实在文字的揉捏下变得弱不禁风。我们在文明的进程中制造了太多的谎言和曾经以为的真理。最为可悲的是,当这原有的真理已经被前进的时间证明错误之后,人们还保有一丝懦弱的温存,顾左右而言他,用更加偏激的行为和思想掩盖真相。
文字美化事实。文字的功效奇特,在掩盖事实之余还能够美化事实,造成现代人的视觉、听觉、触觉、感觉的麻木。在《文明》一文中提到:“文明有效地摘除着视、听、嗅、味、触等方面的恶象,进而消除着文字中的恶语,这诚然减轻了人类的一些痛感,却不能从根本上取消任何一道道德难题和政治难题。”[95]用卡夫卡的观点来佐证以上这段话,就是《谈话录》中的那句:“语言不再是粘合剂。……其实,语言只借给活着的人一段不确定的时间。……实际上,它属于死者和未出生者。”最后他说:“伤害语言向来都是伤害感情,伤害头脑,掩盖世界,冷却冻结。”[96]按照卡夫卡的观点,和语言相关的一切活动,包括作家写作、诗人吟诗、平凡的人说话交流,都是借用语言而已,从未真正拥有语言本身。然而文明造就了顽固的人类中心主义,我们自以为自己是文明的主体,可以借助文字美化事实,却忘记了我们只是使用文字的手段,当手段死去,语言和思想才最终粘合。
第三,语言和文字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意识形态化和生活政治化,从而抑制人的本能和欲望。这种抑制会日渐在大众心里产生一种情绪,在《铁娘子》一文中,韩少功这样解释:“文化阉割导向政治绝育,导向政治上的普遍的反叛情绪,即对革命机器人身份于心不甘的情绪。”[97]这正应了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所讲的:“群体永远漫游在无意识的领地,会随时听命于一切暗示,表现出对理性影响无动于衷的生物所持有的激情,它们失去了一切批判能力,除了极端轻信外再无别的特殊可能。”[98]以上这些要素组成了意识形态化和生活政治化的必要条件,也让挣扎在其中的人失去了应有的自由。在《亲近》一文中说:“人的成熟就是接受社会规范的过程,就是学会所谓分寸感即对周围很多事物保持距离的过程——这正是文明教育的目的。”[99]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是,我们距离原初的世界,那种纯粹的生活有多远?去除政治枷锁这一类的人为因素,我们在这种既定的规范、所谓的文明和高贵的话语体系下,是否抛弃了很多原初的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