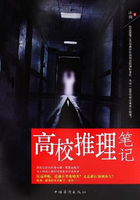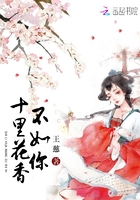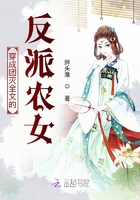前捷克共和国总统哈维尔在其《政治与良心》一文中提及“本来的世界”和“生活的世界”,提到“现代国家和现代政治权力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这里,一旦人类理性从人类个体、他的个人经验、个人责任感中分离出来,他也就背弃了‘本来的世界’的框架,背弃了与之相联的具体的责任感,背弃了他的绝对地平线”。其实,无论是哈维尔笔下的现代国家和现代政治权力,还是韩少功笔下的文化传媒和社会习俗,抑或是桑塔格笔下批驳的过度阐释的文学批评走向,都在证明我们作为人,时时刻刻有意或是无意地被“教会”做什么,怎么活。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意识形态化是文明时代到来的不可避免的产物。
第四,语言文字的出现加剧了社会分层,精英阶层垄断知识。引发了精英主义、民粹主义、反智主义等多种社会思潮。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在《论童年的消逝》一书中警告后人:“我们的孩子不能依靠有权威的成人而是依赖不知从哪里来的新闻来获取知识。我们的孩子还没有提问,就被给予一大堆答案。简言之,我们身边没有儿童了。”[100]语言文字和大众传媒的相继产生,标志着一个日益成熟却日益残忍的时代的到来。原先的口语世界中的知识传播的平等性被抹除,儿童和成人同样暴露在信息之下,同样承受着汹涌而至的海量信息。文盲和知识精英于是被悄悄划分。在中国,随着汉语抽象化的进逼,一个借助文字来建立认知屏障的群体产生,那就是“士族”群体,他们通过科举考试完成社会层级之间的流动。当这群人逐渐占领了社会的话语权的时候,韩少功说:“他们挟万卷经纶投入伟大而艰难的‘文治’,成为一群中国式的文字中心主义者,中国式的‘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 centrism)者’。”[101]相比较而言,“社会不承认农民的艺术品,没收了他们确认和解说更多生活美感的语言能力。”[102]可以说,韩少功的这本《暗示》,就是站在知识分子和农民的双重立场上,反思这种“文字中心主义者”形成的知识垄断和言论霸权。
第五,语言文字的符号化特性导致了大众日常生活的符号化、程式化,实用意义与象征意义的相互取代,以及“语言制幻术”的产生。正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一文中提到的:“技术合理性已经变成了支配合理性本身,具有社会异化于自身的强制本性。……文化工业的技术,通过祛除掉社会劳动和社会系统这两种逻辑之间的区别,实现了标准化和大众生产。”[103]随着文化产业化的进程加快,工业化商业化的生产渗透在文化艺术的各个领域,语言——作为承载艺术文化思想的媒介不知不觉成为罪魁祸首。标准化、大众化、流水线式的生产模式覆盖了人类日常生活的角落。在《M城》一文中,作者对这种批量生产的现象给予这样的评价:“很多精英也就是在这种文化大集里产生的:学位论文是他们的身份证明而不代表他们的兴趣,满房藏书是他们必要的背景而从不通向他们的感情冲动。”[104]他们迷信书,是因为书的象征意义:“古雅、深奥、恒久、清高、有年头、有深度,”[105]而不是它们的实用意义。他们膜拜名片上的头衔名号,是因为它们背后暗藏的权力的掌控,而不是对持有这张名片的人的人格操守的尊敬。他们崇尚各种顶着虚无名头的会议,喜欢空谈主义和思想,实际上却难以掩藏拜金的欲望。
《残忍》一文,揭示了以上表象背后的本质原因:一系列语言符号的复杂操作和反复灌输。[106]当我们吃饭的时候,我们用科学换算表上的数字衡量食物的酸碱度、胆固醇含量和脂肪含量,为的是有一个健康的“不超标”的身体。当我们交流的时候,我们更多地转向电脑屏幕,通过敲打键盘实现远程即时的通讯,而事实是,这种没有情感的字符形似机器的输出。当我们由于种种原因引发战争的时候,我们只需要精良的设备和精准的数据,受攻击的对方,无论人数多少,无论距离多远,无论有多少男女老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都无所谓,因为战士们手中的冷兵器已经放下,他们不需要再像阿基琉斯一样面对赫克托耳的鲜血,他们只需要操纵手中的机器,按下那个红色的按钮,然后面对屏幕上的数据,看着蘑菇云在那里绽放。暴力美学,就在刹那间触手可及。
正因为此,“当被杀者成为一批批可以从容删去的符号时,杀人才可能变成一项无动于衷的作业,不会有任何道德的负罪感。”[107]
文明时代来了。文明时代真的来了么?或者仅仅是另一个因为极度文明造就的蛮荒时代的影像?
以上这些,都是《暗示》给予我的暗示。这本书不厚,却让我在阅读三次之后终于有所体会,形成了上述不完整的文字。这本书不薄,承载着作者对于曾经那个时代的忧虑和愤怒。行文之间,可以嗅到接近野蛮的血腥味,听见作者一声声沉重的叹息。作者说,他似乎更愿意自己走入一个他不可接受的时代,比方走入青铜岁月的边关驿道,在一次失败的战役之后,在马背上看苍山如海残阳如血。而在我合上最后的书页的时候,却看见一个眉宇间写满忧郁无奈的老农民,站在小乡村泥泞的田埂上,赤脚踏着泥土。背后是袅袅炊烟,手中的烟斗沉积着老烟叶。
为思想生活何以可能——读爱德华·萨义德《知识分子论》
“我会告诉你我会做什么和不会做什么。我不会服侍我不再相信的东西,不管那是我的家、我的祖国或我的教会:我要尽可能自由地、完整地以某种生命或艺术的模式来表达自我,用我容许自己使用的仅有的武器——沉默、放逐、狡诈——来自我防卫。”
——乔伊斯
作为一位拥有巴勒斯坦知识分子、欧洲知识分子、大都会知识分子多重身份背景的批判性学者,爱德华·萨义德的学术与政治活动贯穿的一项重要议题即对于“知识分子”的身份体认,因此他的《知识分子论》所阐述的对于知识分子应有的认知、态度与作为之体认与见解对后世影响深远。本文从这本书对于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理解和阐发入手,结合笔者的阅读体会着重论述知识分子的职责及其对政府、公众及其他组织团体应持有的态度,并联系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发展轨迹探讨中国知识分子的未来走向问题。
一、知识分子的“诞生”与内涵分析
“知识分子”(intellectuel)这一概念的诞生始于德雷福斯事件时期的法国。一位名为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的法籍犹太军官在1894年下半年被当做德国间谍蒙冤入狱。在到处弥漫着反犹气氛的大背景下,这种军方制造的冤案原本并不稀奇。然而随着外界对于这一事件的了解日渐深入,尤其是1897年在当时法国文坛声望很高的左拉在一次纪念巴尔扎克的晚会上,在先前了解了各种可靠的材料之后,当众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要求重审此案。与此同时,他在《费加罗报》上连续发表文章抨击不公的事件和其造成的不良影响。1898年,针对军事法庭重审此案时做出的不公判决,左拉怒不可遏地向共和国总统费里克斯·富尔写了一封公开信,发表时被冠以“我控诉”的标题。这封控诉信引起了数百名赞同者的联名支持,以此为契机这封信演化为全国性的政治事件,“知识分子”这一名词也由此诞生。[108]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来看萨义德对于知识分子的阐述就更加清晰和明确。那么,何谓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需要在社会中扮演怎样的角色?承担什么职责?首先,一个具有正义感和使命感的知识分子应当在恰当的时候义不容辞地从事批评、维持应有的立场。在《知识分子论》的译序中写到萨义德本人曾在因参与政治活动多次遭到死亡威胁的情况下说:“……我认为主要的就是坚持不懈,谨记自己的所言所行远比是否安危意义重大。”[109]本书的题目“Representations”(原名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本身就具有以下含义:为民喉舌,作为公理正义及弱势者/受迫害者的代表,及时面对艰难险阻也要向大众表明立场及见解;知识分子的言行举止也代表/再现自己的人格、学识与见地。[110]可以说,知识分子的这种批判和反抗意识在诞生之初就得以确立,不仅是其自身在这一群体和社会中能够获得身份认同的关键,也是外界公众对其角色的规约和期待,即知识分子不能仅仅满足于自身表达诉求的情感抒发,还要将这种抒发同理性的思考相结合,形成坚定的道德立场,对抗不正当的行为或政权。因此,萨义德将这种精神称作“反对的精神(a spirit of opposition)”,而非“调适(accommodation)的精神”。[111]诚然,前者的要求远比后者要高,主要因其涉及知识分子个人利益甚至生命安危。
其次,知识分子应当是独立的,拥有自由的意志。这一标准的现实要求就是处理好同政权、团体组织和社会的关系。萨义德将这一关系称作“流亡者”和“边缘人”(exile and marginal)。他列举文学作品中的例子来说明,其中之一是乔伊斯的《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的爱尔兰年轻人戴德勒斯将“魔鬼式的我不效劳”作为格言。[112]要达到这一标准首先就需要知识分子远离特定的身份、利益以及日常事务的惯例。而在贾克比的《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中以美国为背景提出了这一做法的阻碍之一即“学院知识分子”的兴起。或许是过犹不及和其他意义上的偏离本意,这个群体被贾克比描述成“怯懦、满口学术”,却没有引起社会上的公众的重视。[113]分工日益细密的学科形成了封闭的话语体系,这使得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和沟通尤为不易,也加重了学科内部系统的人成为具有一定专长的技术工人的现象。学科间的分歧已经不仅限于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而渗透到各个学科领域中。事实上,针对独立和自由这一知识分子所需具备的特点而言,最难也是最高的标准是刘易斯·科塞(Lewis Coser,1913-2003)提出的:“知识分子是从来不对现状满意的人,为思想而活,而不是靠思想生活。”为思想生活可以从思想和真理本身的发现和坚持获得极大的愉悦感和幸福感,并且能够不为外物所动,保持相对独立的立场;而靠思想而活则是以思想作为消费品或是交换手段,获得功名利禄;或从属于某一团体或组织,从中得到职位的晋升。只有从以上这些桎梏中脱离出来,知识分子才有实现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可能。
最后,知识分子对于真理有着执着的坚持,有勇气责难一切有悖于公平、正义、人道的行径,并不因为是自己的政府而停止发难。在必要的时候,知识分子甚至可以进行“自我嘲讽”,用他特有的抗拒意识(a resistant consciousness)来获得真理或是坚持立场。此外,对于世界和所处环境的思考、对社会的长期不满也构成了知识分子的一项行为习惯。比如在《何谓欧洲知识分子》一书中,沃尔夫·勒佩尼斯指出,知识分子的天职是抱怨,长期生活在“忧郁”与“乌托邦”之间。前者是对于世界和大众生存状态的担忧,后者是在这种担忧的基础上建立的幻想。[114]如前所述,知识分子角色的复杂性在于他的“疏离”属性,即他必须在理想与现实、服膺与反叛、精英与大众之间做出权衡和抉择。这使得这一角色在当今这个娱乐至上、利益为先的消费社会,尤其在当下的学院语境中也尤为艰难。因为那不仅会被视为是自恃清高的自负和不合群,也会被各种政治力量束缚、意识形态的压倒性优势降服。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群以此为生的群体。在这样的现实面前,复又回想起北宋理学家张横渠先生的那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笔者看来,知识分子在不同的政治背景和文化语境下都具有双向性的内涵:内转,即建立个人修为、提升自我品性以安身立命;外推:即重建社会精神价值、为民众确立生命意义而完成君子人格(如:推己及人、由个人推及家国的意识)的实现。
二、中国知识分子的发展轨迹及生存状况
美国芝加哥大学艾恺教授为其著作《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一书校订编排时曾专访梁漱溟先生十余次,最后集结成《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一书。在交谈采访期间,梁漱溟先生曾说:“深深地进入了解自己,而对自己有办法,才得避免和超出了不智与下等。——这是最深渊的学问,最高明最伟大的能力或本领。然而却不是一味向外逐物的西洋科学家之所知矣。”
这些于自己所在领域发挥巨大能量、在人类思想史上做出杰出贡献、甚至是推动一个时代的进程的精英们的共同特质,在笔者看来,即他们无时无刻不是在寻求清醒的自觉,在任何环境下,甚至是在承受世界格局的动荡、激烈的社会运动的冲击、昏昏大众随波逐流不知所措时,他们都一如既往地思考自身与人类的命运,思考安身立命的道德哲学,从而获得心智的高度圆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