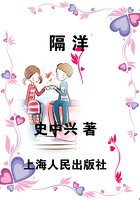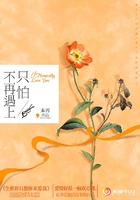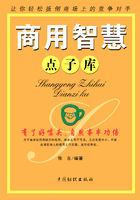热天,铁皮船行在灰白的江面,两岸已不见风景,只见“发展”,江上漂着采砂船,山上山下,到处是开挖的工地,只有临江的红土山岩,偶尔露出石人的眼睛、石狮子的胡须。
船上人不多,大多是老人带着孩子,大家都去新津。一个卖菜的老汉,大箩筐里仅剩几根丝瓜。我问丝瓜多少钱一斤。他说:“今天啊,一块三一斤,卖了一百多斤。”这是2013年8月23日下午两点,从云阳到新津的船上。老城的丝瓜,卖一块三一斤。
我又问新津口有没有旅社。他们告诉我,王振贵家开的旅社,可以去那里吃包面[56]。
这位卖菜的老汉爱逗乐,喜欢故弄玄虚。我跟他斗智斗勇,还是问出了几个好故事——
在庙矶子江边有三块石,石缝中会自动吐米,中间可以坐五席、七席,够你吃的。但有一次,有人贪心,吃饱了还要,并用棍棒敲打三块石,后来石缝就再不出米了。
东羊子本来是一群羊子,你一赶它就变成一堆石头,你不赶,它又是一群羊,在江边吃草。后来地质队的人来寻宝,想把羊子捉去,结果羊子被撵下河。以后东羊子就再也不出人才了。
新津的地势是一只天鹅,当年有一员飞天大将就埋在这里。这一带本来要出霸王的。谁能看破这个地势,埋在那里,后人必定发达。
老汉又说:“几年前在船上也见过一个能干人,跟你一样,留着跨耳胡,专门听老人摆经。”我怀疑那就是从前的自己,也不一定。而无论是谁,他都在鼓励我前行。
“三人行必有我师。”在去往新津的小船上,十来个人当中,我至少找到三位老师。随后一位名叫王祖和,我问起来,他就跟我讲起家族历史——
“新津从前叫新津口,我们老家就在新津口宝塔(乡),到我这里,都是十辈高头了[57],都是在长江边挖泥巴、务农。我们祖上是湖广人,早先是王青、王林两兄弟上川,就落在新津口。祖坟都还在,坟上立的碑,碑上刻的字派:守、思、道、德、正、大、光、宗、耀、祖、永、兴、长、发、士、昌、福、禄、寿、考、运、康、锦、江。祖坟的地势是二龙抢宝。”
“我爷爷叫王宗炳,父亲叫王耀培,都是在新津口种地。我父亲才一岁半,爷爷就去世了,我老头孤身一人,发下来五兄弟(要是不死的话,一共九个,死了两兄弟、两个妹妹)。我母亲也只活到四十五岁,那时候集体生产,她在坡上割蓑草(编绳子用的),溜下来摔倒,中了风,回来三天就死了。我那时十几岁,还在故陵做木工,今年要满七十了。”
“因为家里穷,我只读了两年书,在太盛石桌子(小地名)。石桌子有张石桌子,是从土里挖出来的,上头还雕的花,后来供在太盛庙里。解放前,太盛庙有个庙佬,整天提灯照庙。有一回敲锣鼓‘忌戊’[58],说那几天砍柴、割草的,推磨、纺线的,都不能破土动工,也不能挖泥犁田……
“1949年我们分到地,没分房子,自己有个茅草屋。解放前,我们家种的是地主王守富、王先陶父子的地,我们都喊他们老板。新津口没有大地主,老板父子解放后也没有枪毙。”
“1958年大办钢铁的时候我还在放羊,父亲去了故陵的红光铁厂,抬石头、炼铁……也是1958年进伙食团,一个队一起吃饭,一个人一天二两小谷[59]。一盆苞谷面糊糊,很清,一人舀一勺……我嫂嫂用白鳝泥烙的粑粑,那个白家伙、糯家伙我吃过,不能多吃,多吃了屙不出。普安卫生院的胡医生说,一个人可以吃三四个,和了菜的。灾荒年,再聪明的人,都上过那个当……”
“我们是新津太平大队五队。六队的陈振国、陈振泰、陈振民、陈振安四兄弟家里几乎全饿死了,陈振国家七口人只剩下两娘母,陈振民家只剩下一个儿陈启富。陈振泰、陈振安家,都死绝了。我哥哥王祖青、嫂嫂邱绪贤家里,四个儿、一个女儿都饿死了。”
“灾荒年跟现在一样,”旁边一位老人又说,“青年人没在屋,屋里尽是老人、娃儿。赶牛去地里挖红苕,挖不出几个,生产没有劳力,人都炼钢铁去了。”说话的老人名叫王国强,他们家的字派是:臣、忠、祖、仁、德,寿、康、士、克、昌,国、正、天、下、顺……
多么美好的家族心愿!
临下船的时候,女船员王献春(1962年出生)指着江岸告诉我:“新津是一座乡镇,原先江边的老房子都淹没了。我们家在普安,就在小河出去不远,那里也属于淹没区,地势在175米水位线以下——山上的搬得多,都迁到外地去了;下头的水淹移民搬得少,我四兄弟,两个迁到湖北宜昌,还有两个后靠,我们也属于后靠移民……”
“普安,我还没去,”我说,“我一定要去。”说话间,新津口到了。
下了船,老人领着孩子回家,我被热风吹到江边夕阳下。人在江边,感觉古老的一切近在眼前,历久弥新,生命与时空合一。
山坡有座庭院,我走上去,一位中年男子像是正在那里等我——他独自坐在院子里,旁边是一所小学,学生已经放假,校园里仍飘着五星红旗。我上前询问,先生就告诉我,他叫魏光礼,1951年出生。而随后他又说道:“我们家族的字派是:民、良、佐、太、光、大、文、绪、思、德、有、公。爷爷叫魏佐庭,父亲叫魏太平,从前都是跑船,爷爷、父亲都只活到五十多岁。我们都没见过爷爷。爷爷葬在帽儿山,小地名叫堤坝梁,现在已经淹没了。一些人之前用水泥把坟墓包起来,也没起到作用——坟墓长期浸泡在水里面,那个浪打过来,都要淹没。父亲1985年去世,埋在原先的三王庙,国家后来在那里办了一个老年福利院。”我们说话时,几个孤寡老人在一旁转悠,看上去有些凄惨,原来他们正是福利院里的老人。
“新津口原先是个红火码头,”魏光礼接着说,“老街有一百三十多米,都是石板路,街上大多是木头房子,也有青砖房子,居民总共一千多人,做点小生意,卖粮油米面,开杂货铺、纸货铺的都有。从恩施、利川、思南进出,都要经过新津口,运送米粮、桐油,各种蔬菜、水果,这里的柚子比较多。解放前只有一个甲保长。人们在河滩上求点衣食,也没有太富裕的。我们家自己有条木帆船(帆有十多米高),雇了十几个小伙计(也不算雇,就是大家互相配合,样样货都运);从云阳老城,上到重庆,下到武汉,上海也去过。过去从新津口到云阳老城(上水),如果顺风,一个钟头就到了,回来(下水)就更快了。”
“解放后,新津成立了木船社,客货分装,还是人工用索索拉,我们都拉过,拉滩就跟到嗨咗、嗨咗地喊,拉到一个回水沱,水慢下来,就可以松口气了,喊伙计们,哦——嚯——哦——嗨……后来有了机动船,木船和人力拉纤就逐步被淘汰了。”
“新津口山多,地势是一只天鹅。滩不算险,风平浪静的。险滩在下游的庙矶子、鸡耙子,那里的河床上有些暗礁。这里1982年融山[60],把长江都堵塞了,冷冻厂都冲到河里去了。后来通过长航局炸开泥石,加上德国支援我们的挖沙船,才疏通河道,但地势都变了。”
“我才三四岁,父亲就把我带到船上去玩,到老城、双江;后来我就在新津读书,只读了两三年;十二三岁就开始在农村挖泥培土,搞农田基建。赶上大跃进、灾荒年,我们还小,也吃过那个苦……”
“1958年大办钢铁,我们当时去共和(镇)起的高炉。”一位福利院的老人在一旁说,“农民昼夜挑矿石炼铁,炼出些狗儿铁、铁饼饼,还要再炼。一些人打瞌睡,晚上不出去挑,捉到也是打,吊起来打……我们被派到硐(村第)6铁厂炼铁,国家安排你去,你不去不行。把正劳力都调去了,家里只有老的和小的,种不出庄稼,就没得吃。国家给了点儿,但还是不够吃。”说话的老人叫姚明芳,从前是算八字的。可如今连自己的出生年月都忘了,也是一种境界。
“人类的生存,要靠每天每顿,”魏光礼又说,“哪怕稀粥,装饱了才能生存,那时连稀粥都没有,草根都弄不到来吃。”
“那个红苕捡起来,泥巴都不揩就摔到嘴里嚼着吃了……”姚明芳老人又说,“沿路爬,沿路死,在田里,在屋里走路也可以饿死……后来政策一开放就好了。”
魏光礼接着说:“我们原先的房屋在底下,两间两退的土砖房子,后来江西援助我们这里的希望小学(新和村小),又看中我们这个凼子[61],2002年建校,把我们的地势占了,也没有合同。本来是好事,但我们自己的小孩儿(孙娃儿)就没在这里,到成都那边读书去了,这里教学质量太差……”魏光礼坐在那里,慢条斯理地说,“我们是平民百姓。我说要再拆(现在这个房子),只有搬到政府里去住了。”
夕阳落在新津码头。我坐在魏光礼家的小院子里听他讲述。又来了几位福利院的老人,我起身给他们照相,他们就那样直直地看着我,脸色苍白,胡子拉碴,神态苦涩。
而魏光礼双手交叉,稳坐江边,胸前挂着一个玉牌。他又指给我看他们原先的住处,茫茫江水下的新津老街,谁还能看得清楚?只能看见临水的江岸,三两幢旧屋:一幢青砖房至今完好,坐落在柳荫下;旁边一座土屋深陷草丛,露出几根灰白的木梁,看似一艘搁浅的古船,我真想今晚就住在那里。
当斜阳沉入江水,照亮水中故园,我跟着魏光礼走进新城,身旁的红土高坡像一头伏地狮子,静卧在晚风夕阳里,默默注视着我们,仿佛天黑就要起身,去江上游走。
绕过山坡,走上一座新修的石拱桥,桥下水波清静,映着故园青山——原来新津已安全转移,来到与世无争、世人无从知晓的地方,静候知己问津。
魏光礼告诉我,1982年修的一座旧石桥炸了,现在这座桥下,原先都是老房子,三峡水位上涨之后,都淹没了,还剩一两家。果然,宁静的水边,还能看见一两幢孤单的小房子,白墙蓝瓦,倒映水中。而正当我们在桥上拍照,迎面走来几个中年人。
我上前询问:“这里从前什么样子?”
没想到这些人打量我一番之后,说:“你去找政府问。”
“我不找政府,就找你们。”我说。
“我们就是政府。”他们说。
我暗暗叫苦,原来碰上了乡干部。不一会儿,他们又郑重提醒我:“你要去乡政府报道哦!你想了解的,我们文化站都有,那些划龙船喊号子的,有专门的录音、录像。”说完便扬长而去。而走不多远,其中一个又回过身来说:“各是一行,老师,我怕你不是来搞这个的哦!”
他话里有话,我只有以沉默应对。遇见这样的人,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卑不亢,不去理他。我还是跟着魏大哥继续前行。但没想到遇见这些人之后,魏大哥的态度发生了微妙变化,这我完全能理解。魏大哥还告诉我,从前来过三批记者,都是政府接待的。上个月,重庆还来了一批大学生志愿者,都是学生娃儿,政府接待他们好热情。“他们也给我们拍了照片的,但一直没有寄来。”
尽管如此,他还是将我领到新街。几个孩子正坐在街口玩耍,其中一个赤着脚的小姑娘,抱着一个脏兮兮的洋娃娃,两眼泪汪汪的,像是期待着什么。她叫周欣文,今年五岁了。
天渐渐暗下来,孩子要回家了,我想请魏大哥一起吃晚饭,魏大哥面有难色,说:“这会儿不去了,我去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不能勉强,我又提出想去给先人扫墓。魏大哥不再犹豫,领我来到山坡上,指着山下野草丛中的墓碑说:“瞧,那里就是墓地。”我独自下山,并虔心祭拜。祭如在,我分明感到先人正从土中望着我,为我指点迷津。
我先是拜谒了两座老坟,依山面江,石碑呈黄褐色,上面挂着红纸,因长年日晒雨淋,碑文已经模糊,隐约可见“终身俭朴留典范,一世勤劳传佳风”。四周青草茂盛。而另一处新修的墓园精致典雅,如来世的亭台楼阁,正对着长江,背靠新镇新楼,其中就有魏光礼父母大人的坟墓,上写着:“山青水秀生富贵,龙真穴正发人丁。”而近旁的墓碑上写着:“青山绿水千古秀,福地子孙万代兴。”我在夕阳映照的墓碑前流连,看见江水在石碑上波动。而等我返回,只见魏光礼夫妇俩站在山坡上远远地望着我。
我又跟着他们返回新城,来到王振贵家的旅社。几个包工头正在餐厅里大吃大喝;王振贵老先生亲自上阵,忙得不亦乐乎。我想等他们走了,我好请魏光礼夫妇。
谁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站在门口等着,那一行人又出现在我们身后,并厉声喝斥道:“不许住!你要去政府登记!”——原来这正是先前在桥头撞见的那几个乡政府官员。我假装没听见,但周围的人都听见了。我暗暗叫苦,遇见他们,只有自认倒霉。但无论如何,我不会去他们那里登记,我宁愿睡马路、躺在长江边,也不去他们安排的任何住处。
可谁知这是新津唯一一家私人旅社,他们这一声吼叫,无疑断了我的后路。天黑了,天气炎热,餐厅里依旧红红火火,店家端着盘子进进出出。我就站在眼前,他们视而不见,甚至连头也不抬。深知无望,只得抽身,离开前我暗自发誓,永远不再来这里。
而我去哪里呢?走在新街,我明显感觉到自己正处于众目睽睽之下,陷入尴尬境地:一方面,四周有群众向我围拢靠近,他们显然是有话要说,有情况反映;另一方面,那几个乡干部阴魂不散,一直暗中盯着我,使得周围没人敢接近我。而关键时刻,魏大哥也撤了,好在临走前,他把我托付给一个信得过的老朋友易修全——这位叼着烟、沉默寡言的老先生走在前面,我只有亦步亦趋,跟在他身后。从相貌上看,这位面孔精瘦如雕塑一般的汉子非同寻常,而要让他接受一个陌生人,一个像我这样的不速之客,谈何容易,我心里一点把握也没有。
易师傅默默领我来到家门前,坐在门口乘凉,他还是不说话,只是坐在一边。我还是直奔主题,询问新津现实及历史传说。
路旁的一位妇女说:“我们是农转非移民,家里七八个人,只领到五个人的补助。他们不管你家里几个人,只给五个人的补助。我说都是移民,那几个人不吃饭啊?”可说到这里,她便就此打住。我这才注意到,一些村民正隔着一条马路在暗中望着我,却没有人上前来说些什么。我知道个中缘由:新津只有一条街,谁做什么,说什么,人人都看得见,听得见。
不一会儿,易修全的儿子易朝阳回来,好在这个小伙子什么也不在乎。他和几个小青年在门口支起一口火锅,大家一起涮毛血旺,并邀请我加入。我去旁边小店买来一些啤酒。
酒桌上,易朝阳告诉我:“我们小孩就在新和村希望小学读书,学校只有两个教师,一个叫何少奎何老师,快要退休了,还有一个叫靳远平的小伙子,他们各门课都教。那个年轻的靳老师除了教小学,还教幼儿班……我们这里别的都好,就是教育差。”易朝阳说。我们干杯。很快他又和朋友们谈起生意经,我听不太懂,就傻乎乎地坐在那里。
而等这一桌年轻人渐渐散去,坐在一旁的易修全师傅才慢慢开口——
“从前有种说法:嫁女莫嫁新津口,背柴、挑水,累得大揸口。”
“解放前,新津口有个地主叫魏佐富,是这里的保长,曾经在幺店子那边开个餐馆,后来被弓一孚雇凶杀了——人家叫他运货,他制造翻船假象,骗取货物,后来官司还打赢了;最主要的,还是魏佐富调戏了他的妻子,最后弓一孚就雇凶把他杀了,凶手姓吴……过去好多事情,谁都说不清楚……”
“我小时候就跟父亲一起跑船,后来又参加了老城居民组织的运输队。那时江上,随时都可能打劈船。我们从前还砍竹子、放筏子,从万县放到宜昌的平山坝码头,站在几万斤竹子上,浪打下来,把我们都埋起了也没事儿……”
“1982年五月端午节,我们代表新津口去云阳参加划龙舟比赛,得了冠军,还发了一面旗子的。”易师傅抽着烟,眯着眼睛美美回忆着,“那是云阳县城组织的,去的时候走上水,水流很急,轮船都上不去,我们还是划上去的。别人都穿的救生衣,我们就打个光胴,穿个窑裤[62],滚到江里都不会淹死的……”
“一起比赛的还有长江航运社的、石板根的、双江的、乌杨溪的……人家都是单位出钱,我们新津口的自筹资金,一条船二十多人,各单位的都有。人家大鱼大肉,我们就吃点嫩黄瓜、稀饭馒头,还是搞赢了——横渡长江,从老县城的沙湾划到张王庙……”易修全师傅如是说。而今晚坐在他身边,我依然能感受到当年那份幸福与光荣,那是真正的荣耀,属于易修全,属于新津口。
夜晚,街上已空无一人,我们一同上楼。今晚我就住在易师傅家楼上。简朴的大房间里,一张黑白遗像在暗中望着我们,那目光深情而又凄楚——这是易修全师傅已故的妻子向彩香。
“她只活了五十七岁,阳寿短了些,我还比她大六岁。”易师傅坐下来又点了一支烟,在空荡荡的大房间里轻声说,“我们这个凼子穷,我直到二十七八岁才结的婚,其实她是我的表亲,她妈妈也姓易,家在四方石……人一辈子总得有个伴,还是想两个人,否则就像手臂断了一只……”
沉默良久,易师傅又说:“从前我还认识一个故陵姑娘,姓吴,叫吴淑明,是供销社李家珍介绍的,那是1968年,还在合作化时期,那年八月十五,她来我们家耍,住了七八天,我当时只有一个偏偏屋,她晚上就跟我奶奶住。白天我去生产队做活,天天上坡,自己有自己的事情,她就在屋里耍。她还跟我说,她妈不干,但她背个铺盖就可以过来……临走前她跟我说:‘我明天要走了。’第二天我也没去送她,我一个木箱子都还是她留下的,一直放在那儿。我那时毕竟太年轻,没有懂她的意思。她走了以后来过一封信,说你不让我嫁到新津口,我就嫁到别处去……我也没回信,后来她嫁到河南,我们就再没联系过,确实遗憾……”
“我本来是个粗人,读书读不进去,涮坛子……她也是个老实人,人长得高高的,有点儿胖,跟我妻子差不多,说话还是老实。我也是个老实人。还是个姻缘问题。人生本来就是一出戏,就看唱得好坏……”易修全师傅抽着烟,在暗中轻声诉说。
——原来人活着,可以仅仅只为一份荣誉,一份情怀与眷恋!
而提起现实生活,易师傅只是轻描淡写:“办了养老保险,自己还种点儿丝瓜、南瓜,可以了,是不?”我连连点头,泪流满面。
说到将来,易师傅显得忧心忡忡:“我们这一辈人还过得去,只怕将来(长江)河床逐步上涨,到下一辈,再下一辈,就困难了。现在把土地淹了占了,我说这是害了下一代!——土地没有了,怎么生存?”
是夜,我们在楼上大房间里彻夜长谈,不知不觉,窗口已渐渐泛白。黎明时分,我们又谈及生死之事,“天地君亲”。
易师傅说:“我们家的排行是:维、新、修、礼、义、元、绍、思、真。爷爷和老辈子的坟都在下头,原先的老街后面,都立了碑的;水淹了,还退得出来,但是碑就没再看见。父亲五兄弟,全部都葬在上头的帽儿尖,那里淹不到。父亲落葬的时候条件好些了,一共16个人抬,8个人一轮换。我抬前面,那时我已经七十多岁了,把自己的棺材也买好了。给妻子修坟的时候,我就把我两个修在了一起;修一个也是修,两个也是修,这样还可以减轻后人的负担。我今后一死,只要把泥巴一搓,石头一揭,放进去就行了。我是长江边的人,哪怕我死了,心里还是要看到长江——我那个坟,两边都看得到。爷爷和父亲也都是土葬……生人和死人争地,各有各的打算。今后没了地方,挖出来都是火葬。”
这时,黎明化在窗口,江面一片苍白,新津像一只天鹅,腾空而起,挣脱了人间一切烦恼,飞向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