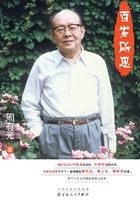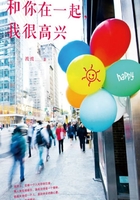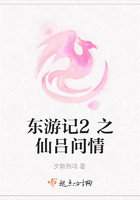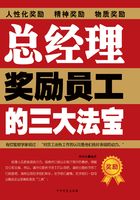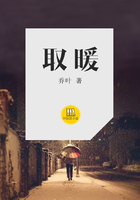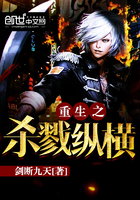公公七十五岁,婆婆七十三岁,他们生在乡村,长在乡村,晚年不肯离开乡村,现在成了空巢老人。“空巢”这个词很形象,儿女们早就“出飞儿”了,两位老人依旧热爱不减地守在老巢里,一如既往地经营着,等待着儿女的假期。移居城市的方案屡提屡否,早成了旧话,如今已无人再提,唯余一根银线,两地牵念。
此生最佩服的人之一是公公,他是个能够适应各种生存环境的人,教师出身,当过校长,却早早把班让女儿接了,故此退休金始终不高。为了生计,他收过废品,爆过玉米花,跑过小买卖,修过自行车,干过农活……他从未否决过儿女的到城里团聚的建议,我觉得他老人家操劳一生,进城过遛遛弯儿、养养鸟儿、钓钓鱼的生活是完全可以的。但公公永远是婆婆手下的听令者和干将,一辈子唯婆婆的马首是瞻。婆婆像极一棵根深蒂固的老榆,任谁也难把她从这片生她养她的土地上起出去。她和我们这些拿工资的人常说一句玩笑话:我这辈子一分钱都没挣到过,真没用!可我敢说婆婆的勤劳不逊于任何一个农村妇女,劳动已成了她的生活习惯,她的手里永远有干不完的活计,除了睡觉,吸烟,陪探家的儿女聊天,就没见她闲过。婆婆半生贫困,对吃穿没有任何奢望,基本是个素食主义者,衣服也大多捡女儿儿媳淘汰下来的。她唯一的爱好和追求是把她的家打理得有条不紊,用她自己的话说是看哪哪舒服。一般农妇都喜欢串门子、扯闲篇儿、打麻将,婆婆一生与此无缘。她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屋舍和园田。无论是住老房子还是新房子,室内永远纤尘不染,这连年轻人都很难做到。婆婆六十八岁上得了脑梗,一条腿走路始终不灵便,但这一点也没影响她劳作。每次回家,看见家里窗明几净的,心里对婆婆的敬佩就油然而生。三间带走廊的房子,前后大窗户,双层玻璃,年逾古稀的她是怎样踩着凳子,登上窗台,反复擦拭的啊!再看看菜园,该有的无一不有,瞅瞅东西两院的蔬菜,没有一家比我们家茁壮。这就是婆婆,她永远都是儿孙无声的榜样,她的居室从不生长脏乱,她的小园从不生长荒芜……
婆婆尽管要强,有一些活她实在干不了,这时她成了指挥官,麾下唯一的战士就是公公了。公公是召之即来,服从命令听指挥,而婆婆是个完美主义者,活儿不满意,严厉的批评是少不了的。每当这个时候,公公大多不吱声,实在吹毛求疵到忍无可忍的地步,老实的公公也会还以颜色,于是两人便吵了起来,结果常常是没有输赢。接下来是漫长的等待,等待儿女们回家评理。他俩矛盾最激烈的时候是春节,这时孩子们都回来了,公公终于闲下来,他要去和老伙伴们打牌。头两天婆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过年了,总要玩一玩的。到了第三天,婆婆如果收到的还是输钱的信息,她的干预行动便开始了。前些年公公因为眼底出血摘除了一个眼球,婆婆一口咬定公公眼神不好,让人把钱都唬去了。“孩子给你俩钱儿,你不输光难受啊?”这是婆婆反复唠叨的一句话。其实公公即使打一个正月的牌,输掉的无非百八十块,一句话,就是没事磨手指头,可由于打牌的场所乌烟瘴气的,加之长时间地坐着,实在于健康无利,所以婆婆唠叨的时候,大家就默然。公公一看没有支持者,也就杀猪不用吹——蔫退(褪)了,不过改为一个人坐在角落里默默看电视罢了。想想公公一年到头生活也忒单调,除了干活就是陪婆婆,还有一个业余爱好是打鱼摸虾,也时不时遭到婆婆的反对,怕他眼睛不好掉沟里,无奈公公没事的时候就不停地织渔网。说起来公公是个心灵手巧的人,他年轻时会书法,识简谱,只不过到了晚年净干粗活了,把那些个雅趣都荒废了。我观察过公公织网,彼时他粗大的手指上下穿梭,灵活极了。偶尔邻居来学,他就像当年教学一样,耐心地指点人家。更多的时候,是他和家庭的另外一些成员打交道,它们是两只鹅,一群鸡,一条狗。他喂养它们,打扫圈舍,和它们唠叨一些无关紧要的话。然后让婆婆把鹅蛋腌上,鸡蛋攒上,留给分散在各地,假期奔向同一个地方的儿孙。
秋天是老两口最忙碌也是最热爱的季节,储菜、腌菜、晾干菜、收拾园子、封闭窗户,活儿多得不得了。劳累加之季节变换,婆婆的咳嗽病常犯。大家劝她戒烟,她说这辈子就这一个嗜好,都七十多岁了,戒不戒都无所谓了。她便一边剧烈地咳嗽,一边扔着她不大听使唤的左腿干活儿。婆婆患脑梗之前走路一阵风一样,从来都是目不旁视,直奔目的地,现在她想快也快不了了。但她的日子充实饱满,从来不知道无聊是什么滋味,今天的活儿干完了,她的大脑又该酝酿明天的计划了。而公公也开始频繁地骑着他的脚蹬三轮车外出,他最喜欢到田野刨树疙瘩或遛土豆。一棵抓紧大地的树墩,得刨多少下子才能挖出来啊!他老人家就那样耐心地一镐一锹刨啊挖啊。我不知他的心里有没有暖暖的火光燃起,有没有另一棵小树葱茏……也许他什么也没想,他的快乐已完全融入到专注里。歇气的时候,他擦擦汗,喝口水,望望远方,轻松惬意就在这劳作的间隙中弥漫……遛土豆是一项令人上瘾的活儿,田角地边,那些被犁杖忽略的地方,往往能找到一窝窝又大又圆的麻土豆,意外的收获、意外的惊喜鼓舞着寻找者,公公就这样在广阔的秋野上乐此不疲,一个秋天下来,运气好的话能有几麻袋的进账。
我们回家去村上的小卖店,店主常常和我们抱怨:你们的父母也太过俭省了,什么东西便宜买什么,又不缺钱,真不知道咋想的。对此公公坚决否认,说没有那八宗事,净胡说。我们知道店主不是胡说,勤俭是深入他们骨髓的东西,即使他们的儿子是百万富翁,也改变不了他们的生活方式。每年的十一月下旬,天已经很冷了,我们打电话过去问他们烧炉子没有,回答是屋子不冷,有火炕呢。婆婆有三个老式板柜,大多装着儿女们穿旧的衣服,她一件也舍不得扔掉,柜子满满登登,她的心就富足安定。
公公婆婆从未出过省,他们大半生的脚印留在了村庄。